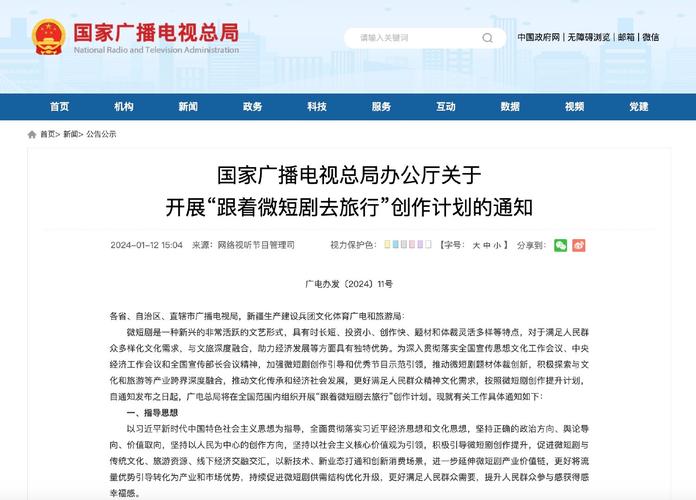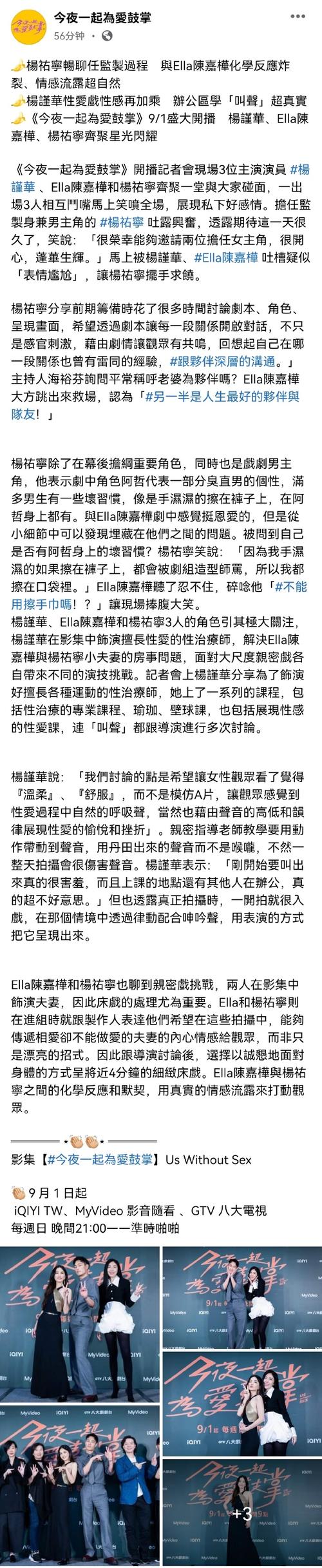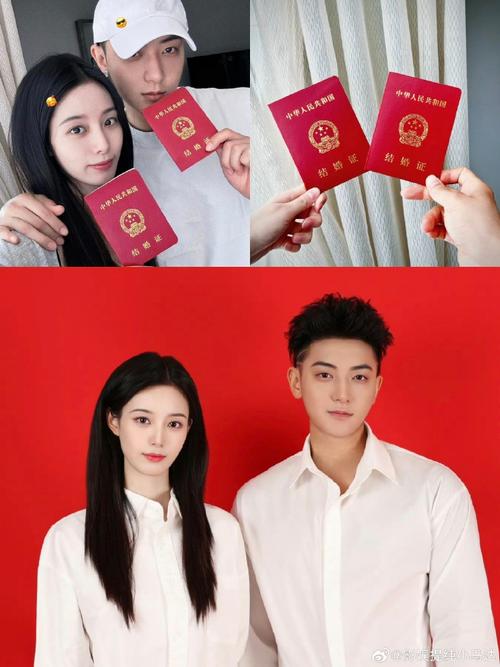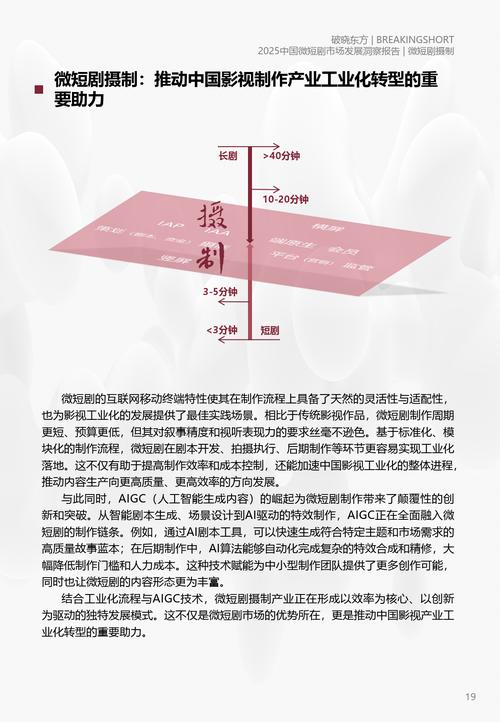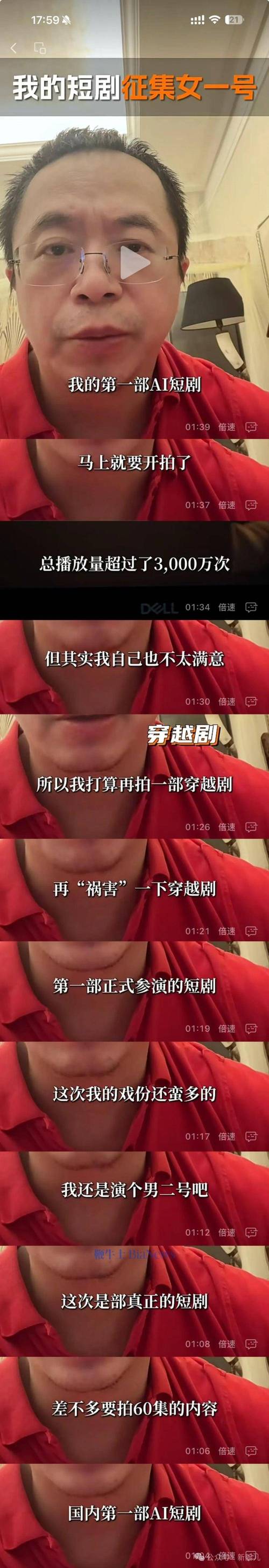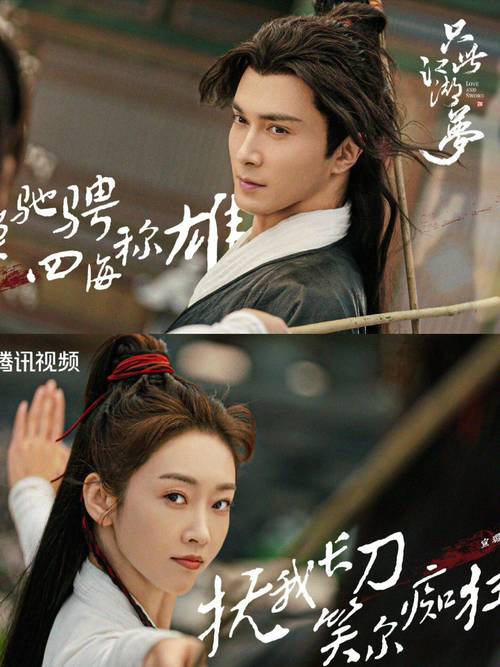《恶意》这部电影,陈思诚监制的,讲的是网上那些坏事儿,怎么把人给害了。故事就是从网上那些事儿来的,一环扣一环,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传、怎么害人,都给**出来了。电影一开始,就是那个滨江三院两个人从楼上下来的事儿,一下子就把人给带进去了,挺紧张。拍手里拿着摄像机,在医院里头跑来跑去,还有那个得癌症的小姑娘,跟护士追来追去,看得人心里头直发怵。那个记者叶攀,也来得很快,把新闻现场那紧张劲儿,搞得跟谍战片似的。事情在网上越传越邪乎。叶攀先发了个“护士推病人下楼”的新闻,一下子就把大家给气坏了,都骂那个护士李悦。接着,有个妈妈在ICU里头犹豫着要不要拔管子的事儿,被人家给剪来剪去,说她是杀人骗保,大家又都骂她。还有一个实习生,造了个假录音,说叶攀怎么怎么坏,怎么把人给害了。这一连串的事儿,就像一个圈儿,受害的,变成害人的,再又有人受害,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人都给吞噬了,**得很清楚。电影在讲新闻也挺实在的。它没整那些传播学的术语,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媒体、流量那些事儿。叶攀是个老记者了,在乱七八糟的环境里头,她**很机灵,说话做事都挺决断,甚至**说挺狠。但这都是因为她知道怎么利用流量,怎么迎合那些规则。这种实在劲儿,也是电影批判的第一层意思,也让角色很有劲儿。为了把事情搞得更有意思,电影还把几种类型给掺和一块儿了。孙越、豆豆他们几个,平时是讲笑话的,在这电影里,他们就是网上那些追着流量跑、没啥底线蹭热度的人。他们干的事儿,看着挺逗,甚至挺可笑,但真实情况是,也是一种小小的坏心思。这种用乐子来衬着悲哀的安排,在笑一下子又觉得后背凉飕飕的。电影要**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它给拍出来,是个挺难的事儿。《恶意》在这方面,做得挺有分寸,也挺有办法。它没整那些血腥的场面,*没老哭哭啼啼的,就是用好多反转来加强矛盾。一开始,那个大学教授的事儿,就有好几个反转,就像个小故事,给后面更大的乱子埋了根子。叶攀在大学里头,被学生给围起来质问,那场戏,气氛很紧张,镜头对着人眼珠子,看得人心里直跳,把被大家骂的压力,转化成很有劲儿的画面。相若是对网上那些又气人又难听的骂声,电影选了一个挺简单但挺管用的视觉符号——就是屏幕上全是弹幕,都是些难听的话。这样处理,虽然技术上不算复杂,但在有限的画面里,把集体发疯的劲儿,**得很清楚,看了心里直发毛。《恶意》最看着很不一样,也挺能看出作者想法的地方,就是它的结局。一般的商业片,都喜欢有个大团圆,好人得救,坏人受罚,但《恶意》的结局,却跟这不一样。它不给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不让好人风光,就是走了一个自己想的事儿。那个实习生,把叶攀给害了,其实是因为叶攀以前也干过不少没底线的报道,没顾上报道的规矩,这下子,自己种的因,结了果,反过来害了自己。这么一个闭环,挺像老戏里的悲剧,看着心里头又沉又闷,也得想是怎么来的,责任在哪儿。这种自己想的事儿,想起陈思诚在首映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外面老给人加上各种“阴谋论”的标签,其实电影就是拍电影的人瞎琢磨,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没那么多阴谋,就是爱拍电影。这话,跟电影里头那个记者的困境挺像的。陈思诚好像也在说自己,在商业和创作之间,也挺挣扎的。他把自个儿的心里话,放到了角色身上,用这么一个不圆满的结局,来反省自个儿。有些人,老把《恶意》跟东野圭吾那个推理小说比。两者说的“坏事儿”,不太一样。东野圭吾那个,是说人心里头那些坏念头,挺没来由的“恶”;但电影**《恶意》,说的是网上系统性的“恶”,不光是个人,还是因为流量那些规则,大家瞎起哄,一个人在大环境里头,也挺没劲儿的。这种“恶”,就是点个鼠标,转个身,为了流量,干点不地道的事儿,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然后就没法控制了。这也是电影想说的。**这么一把刀子,把类型给削得这么薄,也难免会有点问题。它就宿命般地,掉进了一个挺难的坑里——拍电影的,哪赶得上网上那些事儿变那么快。《恶意》从立项到拍完,*就一年多,在拍电影里头,已经挺快了,但它想拍的那些网上的事儿,那些传播的**,那些人的情绪,早就变了。这种天然的,赶不上趟儿的,有时候会觉得,电影里头那些事儿,有点不真实,没那么冲击力了。还有就是性别那点事儿,也被人提出来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是,电影里头,每次要有大反转,要掀起一阵波,都是跟女人有关——护士李悦,那个妈妈,还有叶攀,都是被人说成是坏女人。这**也挺映现实了,现实里头,女人在网上,更容易被人攻击,被审判。这有挺强的现实意义;但从讲故事的角度看,老这么用女人当引爆点,也掉进了一个老套里头?在批判一种暴力,又用了这种攻击女人的暴力当素材?这是电影在讲女人那点事儿上,有点想的事儿。
《恶意》这部电影,陈思诚监制的,讲的是网上那些坏事儿,怎么把人给害了。故事就是从网上那些事儿来的,一环扣一环,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传、怎么害人,都给**出来了。电影一开始,就是那个滨江三院两个人从楼上下来的事儿,一下子就把人给带进去了,挺紧张。拍手里拿着摄像机,在医院里头跑来跑去,还有那个得癌症的小姑娘,跟护士追来追去,看得人心里头直发怵。那个记者叶攀,也来得很快,把新闻现场那紧张劲儿,搞得跟谍战片似的。事情在网上越传越邪乎。叶攀先发了个“护士推病人下楼”的新闻,一下子就把大家给气坏了,都骂那个护士李悦。接着,有个妈妈在ICU里头犹豫着要不要拔管子的事儿,被人家给剪来剪去,说她是杀人骗保,大家又都骂她。还有一个实习生,造了个假录音,说叶攀怎么怎么坏,怎么把人给害了。这一连串的事儿,就像一个圈儿,受害的,变成害人的,再又有人受害,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人都给吞噬了,**得很清楚。电影在讲新闻也挺实在的。它没整那些传播学的术语,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媒体、流量那些事儿。叶攀是个老记者了,在乱七八糟的环境里头,她**很机灵,说话做事都挺决断,甚至**说挺狠。但这都是因为她知道怎么利用流量,怎么迎合那些规则。这种实在劲儿,也是电影批判的第一层意思,也让角色很有劲儿。为了把事情搞得更有意思,电影还把几种类型给掺和一块儿了。孙越、豆豆他们几个,平时是讲笑话的,在这电影里,他们就是网上那些追着流量跑、没啥底线蹭热度的人。他们干的事儿,看着挺逗,甚至挺可笑,但真实情况是,也是一种小小的坏心思。这种用乐子来衬着悲哀的安排,在笑一下子又觉得后背凉飕飕的。电影要**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它给拍出来,是个挺难的事儿。《恶意》在这方面,做得挺有分寸,也挺有办法。它没整那些血腥的场面,*没老哭哭啼啼的,就是用好多反转来加强矛盾。一开始,那个大学教授的事儿,就有好几个反转,就像个小故事,给后面更大的乱子埋了根子。叶攀在大学里头,被学生给围起来质问,那场戏,气氛很紧张,镜头对着人眼珠子,看得人心里直跳,把被大家骂的压力,转化成很有劲儿的画面。相若是对网上那些又气人又难听的骂声,电影选了一个挺简单但挺管用的视觉符号——就是屏幕上全是弹幕,都是些难听的话。这样处理,虽然技术上不算复杂,但在有限的画面里,把集体发疯的劲儿,**得很清楚,看了心里直发毛。《恶意》最看着很不一样,也挺能看出作者想法的地方,就是它的结局。一般的商业片,都喜欢有个大团圆,好人得救,坏人受罚,但《恶意》的结局,却跟这不一样。它不给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不让好人风光,就是走了一个自己想的事儿。那个实习生,把叶攀给害了,其实是因为叶攀以前也干过不少没底线的报道,没顾上报道的规矩,这下子,自己种的因,结了果,反过来害了自己。这么一个闭环,挺像老戏里的悲剧,看着心里头又沉又闷,也得想是怎么来的,责任在哪儿。这种自己想的事儿,想起陈思诚在首映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外面老给人加上各种“阴谋论”的标签,其实电影就是拍电影的人瞎琢磨,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没那么多阴谋,就是爱拍电影。这话,跟电影里头那个记者的困境挺像的。陈思诚好像也在说自己,在商业和创作之间,也挺挣扎的。他把自个儿的心里话,放到了角色身上,用这么一个不圆满的结局,来反省自个儿。有些人,老把《恶意》跟东野圭吾那个推理小说比。两者说的“坏事儿”,不太一样。东野圭吾那个,是说人心里头那些坏念头,挺没来由的“恶”;但电影**《恶意》,说的是网上系统性的“恶”,不光是个人,还是因为流量那些规则,大家瞎起哄,一个人在大环境里头,也挺没劲儿的。这种“恶”,就是点个鼠标,转个身,为了流量,干点不地道的事儿,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然后就没法控制了。这也是电影想说的。**这么一把刀子,把类型给削得这么薄,也难免会有点问题。它就宿命般地,掉进了一个挺难的坑里——拍电影的,哪赶得上网上那些事儿变那么快。《恶意》从立项到拍完,*就一年多,在拍电影里头,已经挺快了,但它想拍的那些网上的事儿,那些传播的**,那些人的情绪,早就变了。这种天然的,赶不上趟儿的,有时候会觉得,电影里头那些事儿,有点不真实,没那么冲击力了。还有就是性别那点事儿,也被人提出来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是,电影里头,每次要有大反转,要掀起一阵波,都是跟女人有关——护士李悦,那个妈妈,还有叶攀,都是被人说成是坏女人。这**也挺映现实了,现实里头,女人在网上,更容易被人攻击,被审判。这有挺强的现实意义;但从讲故事的角度看,老这么用女人当引爆点,也掉进了一个老套里头?在批判一种暴力,又用了这种攻击女人的暴力当素材?这是电影在讲女人那点事儿上,有点想的事儿。陈思诚监制《恶意》 现实题材揭露网络暴力,结局震撼引人深思
 《恶意》这部电影,陈思诚监制的,讲的是网上那些坏事儿,怎么把人给害了。故事就是从网上那些事儿来的,一环扣一环,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传、怎么害人,都给**出来了。电影一开始,就是那个滨江三院两个人从楼上下来的事儿,一下子就把人给带进去了,挺紧张。拍手里拿着摄像机,在医院里头跑来跑去,还有那个得癌症的小姑娘,跟护士追来追去,看得人心里头直发怵。那个记者叶攀,也来得很快,把新闻现场那紧张劲儿,搞得跟谍战片似的。事情在网上越传越邪乎。叶攀先发了个“护士推病人下楼”的新闻,一下子就把大家给气坏了,都骂那个护士李悦。接着,有个妈妈在ICU里头犹豫着要不要拔管子的事儿,被人家给剪来剪去,说她是杀人骗保,大家又都骂她。还有一个实习生,造了个假录音,说叶攀怎么怎么坏,怎么把人给害了。这一连串的事儿,就像一个圈儿,受害的,变成害人的,再又有人受害,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人都给吞噬了,**得很清楚。电影在讲新闻也挺实在的。它没整那些传播学的术语,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媒体、流量那些事儿。叶攀是个老记者了,在乱七八糟的环境里头,她**很机灵,说话做事都挺决断,甚至**说挺狠。但这都是因为她知道怎么利用流量,怎么迎合那些规则。这种实在劲儿,也是电影批判的第一层意思,也让角色很有劲儿。为了把事情搞得更有意思,电影还把几种类型给掺和一块儿了。孙越、豆豆他们几个,平时是讲笑话的,在这电影里,他们就是网上那些追着流量跑、没啥底线蹭热度的人。他们干的事儿,看着挺逗,甚至挺可笑,但真实情况是,也是一种小小的坏心思。这种用乐子来衬着悲哀的安排,在笑一下子又觉得后背凉飕飕的。电影要**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它给拍出来,是个挺难的事儿。《恶意》在这方面,做得挺有分寸,也挺有办法。它没整那些血腥的场面,*没老哭哭啼啼的,就是用好多反转来加强矛盾。一开始,那个大学教授的事儿,就有好几个反转,就像个小故事,给后面更大的乱子埋了根子。叶攀在大学里头,被学生给围起来质问,那场戏,气氛很紧张,镜头对着人眼珠子,看得人心里直跳,把被大家骂的压力,转化成很有劲儿的画面。相若是对网上那些又气人又难听的骂声,电影选了一个挺简单但挺管用的视觉符号——就是屏幕上全是弹幕,都是些难听的话。这样处理,虽然技术上不算复杂,但在有限的画面里,把集体发疯的劲儿,**得很清楚,看了心里直发毛。《恶意》最看着很不一样,也挺能看出作者想法的地方,就是它的结局。一般的商业片,都喜欢有个大团圆,好人得救,坏人受罚,但《恶意》的结局,却跟这不一样。它不给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不让好人风光,就是走了一个自己想的事儿。那个实习生,把叶攀给害了,其实是因为叶攀以前也干过不少没底线的报道,没顾上报道的规矩,这下子,自己种的因,结了果,反过来害了自己。这么一个闭环,挺像老戏里的悲剧,看着心里头又沉又闷,也得想是怎么来的,责任在哪儿。这种自己想的事儿,想起陈思诚在首映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外面老给人加上各种“阴谋论”的标签,其实电影就是拍电影的人瞎琢磨,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没那么多阴谋,就是爱拍电影。这话,跟电影里头那个记者的困境挺像的。陈思诚好像也在说自己,在商业和创作之间,也挺挣扎的。他把自个儿的心里话,放到了角色身上,用这么一个不圆满的结局,来反省自个儿。有些人,老把《恶意》跟东野圭吾那个推理小说比。两者说的“坏事儿”,不太一样。东野圭吾那个,是说人心里头那些坏念头,挺没来由的“恶”;但电影**《恶意》,说的是网上系统性的“恶”,不光是个人,还是因为流量那些规则,大家瞎起哄,一个人在大环境里头,也挺没劲儿的。这种“恶”,就是点个鼠标,转个身,为了流量,干点不地道的事儿,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然后就没法控制了。这也是电影想说的。**这么一把刀子,把类型给削得这么薄,也难免会有点问题。它就宿命般地,掉进了一个挺难的坑里——拍电影的,哪赶得上网上那些事儿变那么快。《恶意》从立项到拍完,*就一年多,在拍电影里头,已经挺快了,但它想拍的那些网上的事儿,那些传播的**,那些人的情绪,早就变了。这种天然的,赶不上趟儿的,有时候会觉得,电影里头那些事儿,有点不真实,没那么冲击力了。还有就是性别那点事儿,也被人提出来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是,电影里头,每次要有大反转,要掀起一阵波,都是跟女人有关——护士李悦,那个妈妈,还有叶攀,都是被人说成是坏女人。这**也挺映现实了,现实里头,女人在网上,更容易被人攻击,被审判。这有挺强的现实意义;但从讲故事的角度看,老这么用女人当引爆点,也掉进了一个老套里头?在批判一种暴力,又用了这种攻击女人的暴力当素材?这是电影在讲女人那点事儿上,有点想的事儿。
《恶意》这部电影,陈思诚监制的,讲的是网上那些坏事儿,怎么把人给害了。故事就是从网上那些事儿来的,一环扣一环,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传、怎么害人,都给**出来了。电影一开始,就是那个滨江三院两个人从楼上下来的事儿,一下子就把人给带进去了,挺紧张。拍手里拿着摄像机,在医院里头跑来跑去,还有那个得癌症的小姑娘,跟护士追来追去,看得人心里头直发怵。那个记者叶攀,也来得很快,把新闻现场那紧张劲儿,搞得跟谍战片似的。事情在网上越传越邪乎。叶攀先发了个“护士推病人下楼”的新闻,一下子就把大家给气坏了,都骂那个护士李悦。接着,有个妈妈在ICU里头犹豫着要不要拔管子的事儿,被人家给剪来剪去,说她是杀人骗保,大家又都骂她。还有一个实习生,造了个假录音,说叶攀怎么怎么坏,怎么把人给害了。这一连串的事儿,就像一个圈儿,受害的,变成害人的,再又有人受害,把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人都给吞噬了,**得很清楚。电影在讲新闻也挺实在的。它没整那些传播学的术语,也老老实实承认自媒体、流量那些事儿。叶攀是个老记者了,在乱七八糟的环境里头,她**很机灵,说话做事都挺决断,甚至**说挺狠。但这都是因为她知道怎么利用流量,怎么迎合那些规则。这种实在劲儿,也是电影批判的第一层意思,也让角色很有劲儿。为了把事情搞得更有意思,电影还把几种类型给掺和一块儿了。孙越、豆豆他们几个,平时是讲笑话的,在这电影里,他们就是网上那些追着流量跑、没啥底线蹭热度的人。他们干的事儿,看着挺逗,甚至挺可笑,但真实情况是,也是一种小小的坏心思。这种用乐子来衬着悲哀的安排,在笑一下子又觉得后背凉飕飕的。电影要**网上那些坏心思,怎么把它给拍出来,是个挺难的事儿。《恶意》在这方面,做得挺有分寸,也挺有办法。它没整那些血腥的场面,*没老哭哭啼啼的,就是用好多反转来加强矛盾。一开始,那个大学教授的事儿,就有好几个反转,就像个小故事,给后面更大的乱子埋了根子。叶攀在大学里头,被学生给围起来质问,那场戏,气氛很紧张,镜头对着人眼珠子,看得人心里直跳,把被大家骂的压力,转化成很有劲儿的画面。相若是对网上那些又气人又难听的骂声,电影选了一个挺简单但挺管用的视觉符号——就是屏幕上全是弹幕,都是些难听的话。这样处理,虽然技术上不算复杂,但在有限的画面里,把集体发疯的劲儿,**得很清楚,看了心里直发毛。《恶意》最看着很不一样,也挺能看出作者想法的地方,就是它的结局。一般的商业片,都喜欢有个大团圆,好人得救,坏人受罚,但《恶意》的结局,却跟这不一样。它不给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不让好人风光,就是走了一个自己想的事儿。那个实习生,把叶攀给害了,其实是因为叶攀以前也干过不少没底线的报道,没顾上报道的规矩,这下子,自己种的因,结了果,反过来害了自己。这么一个闭环,挺像老戏里的悲剧,看着心里头又沉又闷,也得想是怎么来的,责任在哪儿。这种自己想的事儿,想起陈思诚在首映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外面老给人加上各种“阴谋论”的标签,其实电影就是拍电影的人瞎琢磨,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没那么多阴谋,就是爱拍电影。这话,跟电影里头那个记者的困境挺像的。陈思诚好像也在说自己,在商业和创作之间,也挺挣扎的。他把自个儿的心里话,放到了角色身上,用这么一个不圆满的结局,来反省自个儿。有些人,老把《恶意》跟东野圭吾那个推理小说比。两者说的“坏事儿”,不太一样。东野圭吾那个,是说人心里头那些坏念头,挺没来由的“恶”;但电影**《恶意》,说的是网上系统性的“恶”,不光是个人,还是因为流量那些规则,大家瞎起哄,一个人在大环境里头,也挺没劲儿的。这种“恶”,就是点个鼠标,转个身,为了流量,干点不地道的事儿,一下子就火起来了,然后就没法控制了。这也是电影想说的。**这么一把刀子,把类型给削得这么薄,也难免会有点问题。它就宿命般地,掉进了一个挺难的坑里——拍电影的,哪赶得上网上那些事儿变那么快。《恶意》从立项到拍完,*就一年多,在拍电影里头,已经挺快了,但它想拍的那些网上的事儿,那些传播的**,那些人的情绪,早就变了。这种天然的,赶不上趟儿的,有时候会觉得,电影里头那些事儿,有点不真实,没那么冲击力了。还有就是性别那点事儿,也被人提出来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是,电影里头,每次要有大反转,要掀起一阵波,都是跟女人有关——护士李悦,那个妈妈,还有叶攀,都是被人说成是坏女人。这**也挺映现实了,现实里头,女人在网上,更容易被人攻击,被审判。这有挺强的现实意义;但从讲故事的角度看,老这么用女人当引爆点,也掉进了一个老套里头?在批判一种暴力,又用了这种攻击女人的暴力当素材?这是电影在讲女人那点事儿上,有点想的事儿。
广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