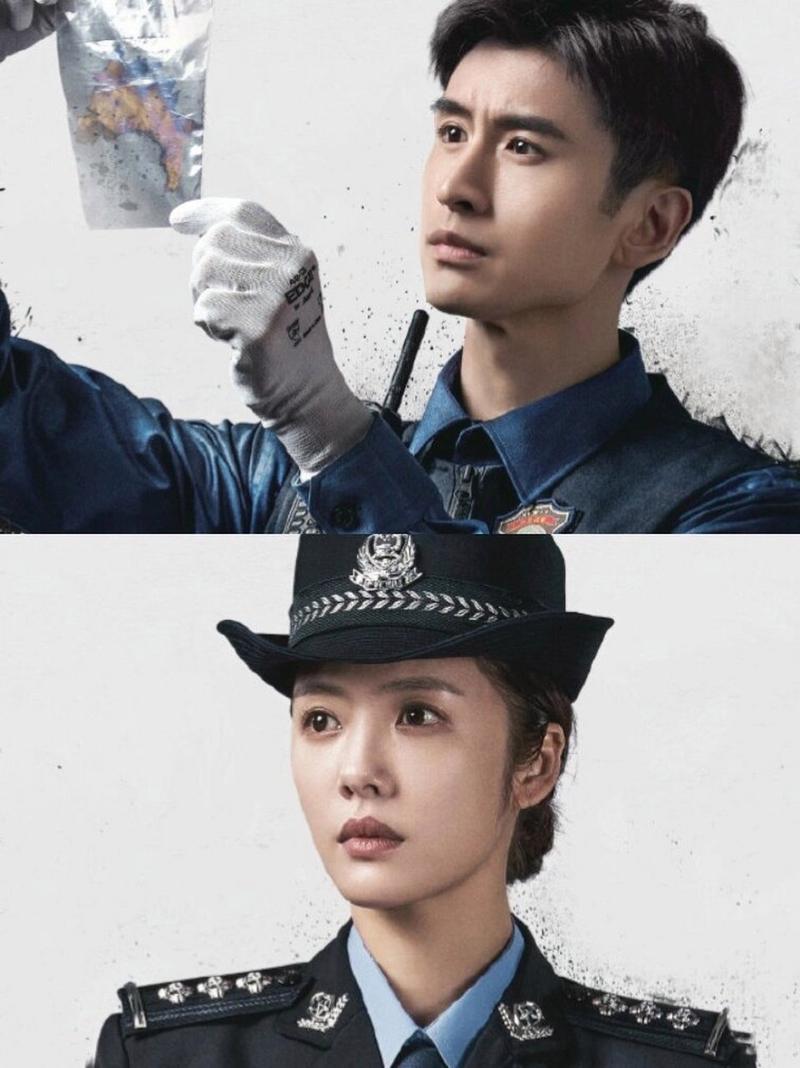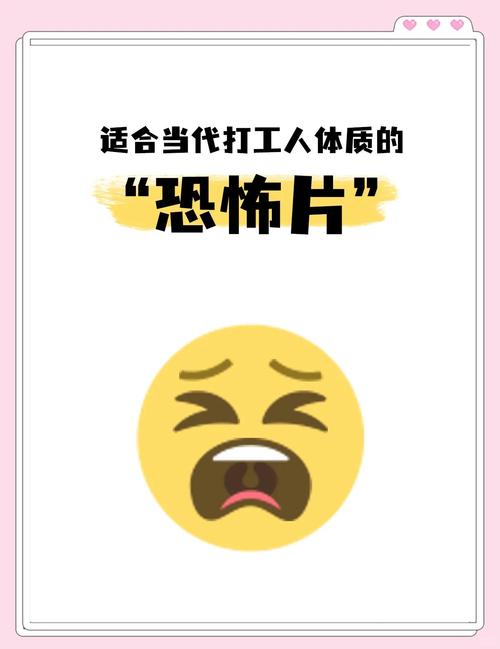 最近去电影院,大银幕上净是些讲打工人 movies。有部《长安的荔枝》,主角李善德在大唐忙活,从长安跑到岭南,反复做试验,就为让贵妃吃上新鲜荔枝。还有《戏台》,讲个戏班子在民国乱糟糟的职场,洪大帅一句话改戏,把戏班子搞得死去活来。还有《浪浪山小妖怪》,四个小妖怪在妖怪公司里瞎折腾,考编、冒名顶替去西天取经,拼死拼活想混出个人样,**连名字都留不下。不同地方的打工人,在不同类型的 movies 里拼死拼活,就想有个盼头。有人就说,2025年是“打工人电影”元年。看,《浪浪山小妖怪》票房破7亿,《戏台》快4亿,《长安的荔枝》超6亿,真有点“得打工人者得票房”的意思。但微博上,不光是打工人 movies 有声音。这类 movies 争议*大,成了最近网上的一道风景线。打工人 movies,四大特点明明白白。本来没打工人赛道,这类 movies 拍多了,就***赛道。要是找起点,要是2023年的《年会不能停!》。这部片票房近13亿,把互联网黑话、大厂那套,还有当代职场风气都给揭开了,豆瓣评分8.1,叫好又叫座。同年的《银河写手》也算同类,就是全是行业黑话,观众不买账,票房就几百万。2024年,《逆行人生》和《胜券在握》又来了。一个讲程序员被裁去送外卖,一个讲被裁员工斗老板,都把赛道扩大了。今年,《长安的荔枝》《戏台》《浪浪山小妖怪》这些,古装的、动画的都有,甚至有部《诡才之道》,主角死了还当鬼,照样要考核、评奖、晋升。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大致就这四大特点:设定基于职场现实,内容荒诞讽刺,形式爱用喜剧,价值观强调人尊严。设定基于现实,观众才有共鸣。荒诞讽刺和喜剧紧挨着,*好理解。打工本来就累,拍成纪录片更累,喜剧就是给打工人苦痛裹层糖衣。至于价值观上强调主角尊严,更**照顾观众情绪,看完不光绝望,还有个情绪出口。同一部打工人电影,观众**不同。 movies 爱这类题材,但多的打工人看腻了这套叙事。社交平台上,***说看完《浪浪山小妖怪》眼泪都出来了,感觉在电影院被攻击了。一个做设计的人张扬(化名)说,看到公鸡画师的桥段就“破防”了。他日常工作就是画图,甲方跟电影里猪妖没啥区别,要求画出“取经人的感觉”,又不说要啥。反复折腾,最后用第一版,真头大。对他来说,看多了头疼,想多了心疼。中部某省会的影城经理冬阳(化名)说,今年暑期档打工人影片扎堆,是创作上不约而同。 《年会不能停!》火了,同类题材项目一上马,今年就集中爆发了。在他看来,题材不是万能的,重点还得讲好故事。像2024年的《胜券在握》,讲裁员、斗老板,但内容太飘,观众不买账。资深电影人连城易脆说,短期内这么多“打工人电影”确实代表趋势和社会情绪,但也不能忽略偶然性。《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小说,《浪浪山小妖怪》脱胎于《中国奇谭》系列短片,《戏台》**有2015年的话剧版。这些故事都有各自完善过程,不是期创作的。经济下行期,社会更**普通人生活心态。电影给无声者立言,多拍打工人电影,们被看到,总归是好事。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也有一千种打工人。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有人被逗得哈哈大笑,有人笑不出来。打工人赛道兴盛,是创作者抓住社会思潮,也是 movies 题材内卷**。一部电影选职场背景,自带流量,多人想分一杯羹。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多样,对职场困境**真实。这太可怕了。本来打工人生活就麻木,还要花钱去电影院照镜子。工作已经够累了,还有多少人想到电影院来“受罪”?那些上班上进之间选上香的观众,看“打工人电影”真会不适。更重点的是,“打工人电影”内在结构有缺陷。从《年会不能停!》开始,这类电影都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打工人困境,最后只能靠“机械降神”或幻想解决。《年会不能停!》结尾,主角团全靠董事长一句话逆袭。《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摆脱“长安的浮萍”,是靠被发配岭南,阴差阳错躲过“安史之乱”。《戏台》里,五庆班不用再受洪大帅折腾,是因为新的大帅打进京城。《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有大招加持,还有大圣保命毫毛。这些都不是普通打工人能遇到的。电影**打鸡血、灌鸡汤,有“爽感”,但再怎么升华也不能掩盖现实无奈:打工人被困在系统里。好比《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说的,工作伦理本质是对自由的摒弃。谋生和自由不能平衡,打工人电影路也会越走越窄。电影是造梦机器,给观众编了解气过瘾的梦,但走出电影院,打工人照样加班、背锅、内耗。一部电影后,那些被嘲讽的内容,像回旋镖一样飞回打工人身上,这才是“打工人电影”最郁闷的地方。直接上甜品的爱情片不行了,大场面视觉片不行了,先苦后甜的职场片也转移不了视线了,横不能天天都是“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就是要你死”的咆哮吧。电影的精神抚慰功能有限,现实困境还得在现实中解决。这不是空话,是修行。
最近去电影院,大银幕上净是些讲打工人 movies。有部《长安的荔枝》,主角李善德在大唐忙活,从长安跑到岭南,反复做试验,就为让贵妃吃上新鲜荔枝。还有《戏台》,讲个戏班子在民国乱糟糟的职场,洪大帅一句话改戏,把戏班子搞得死去活来。还有《浪浪山小妖怪》,四个小妖怪在妖怪公司里瞎折腾,考编、冒名顶替去西天取经,拼死拼活想混出个人样,**连名字都留不下。不同地方的打工人,在不同类型的 movies 里拼死拼活,就想有个盼头。有人就说,2025年是“打工人电影”元年。看,《浪浪山小妖怪》票房破7亿,《戏台》快4亿,《长安的荔枝》超6亿,真有点“得打工人者得票房”的意思。但微博上,不光是打工人 movies 有声音。这类 movies 争议*大,成了最近网上的一道风景线。打工人 movies,四大特点明明白白。本来没打工人赛道,这类 movies 拍多了,就***赛道。要是找起点,要是2023年的《年会不能停!》。这部片票房近13亿,把互联网黑话、大厂那套,还有当代职场风气都给揭开了,豆瓣评分8.1,叫好又叫座。同年的《银河写手》也算同类,就是全是行业黑话,观众不买账,票房就几百万。2024年,《逆行人生》和《胜券在握》又来了。一个讲程序员被裁去送外卖,一个讲被裁员工斗老板,都把赛道扩大了。今年,《长安的荔枝》《戏台》《浪浪山小妖怪》这些,古装的、动画的都有,甚至有部《诡才之道》,主角死了还当鬼,照样要考核、评奖、晋升。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大致就这四大特点:设定基于职场现实,内容荒诞讽刺,形式爱用喜剧,价值观强调人尊严。设定基于现实,观众才有共鸣。荒诞讽刺和喜剧紧挨着,*好理解。打工本来就累,拍成纪录片更累,喜剧就是给打工人苦痛裹层糖衣。至于价值观上强调主角尊严,更**照顾观众情绪,看完不光绝望,还有个情绪出口。同一部打工人电影,观众**不同。 movies 爱这类题材,但多的打工人看腻了这套叙事。社交平台上,***说看完《浪浪山小妖怪》眼泪都出来了,感觉在电影院被攻击了。一个做设计的人张扬(化名)说,看到公鸡画师的桥段就“破防”了。他日常工作就是画图,甲方跟电影里猪妖没啥区别,要求画出“取经人的感觉”,又不说要啥。反复折腾,最后用第一版,真头大。对他来说,看多了头疼,想多了心疼。中部某省会的影城经理冬阳(化名)说,今年暑期档打工人影片扎堆,是创作上不约而同。 《年会不能停!》火了,同类题材项目一上马,今年就集中爆发了。在他看来,题材不是万能的,重点还得讲好故事。像2024年的《胜券在握》,讲裁员、斗老板,但内容太飘,观众不买账。资深电影人连城易脆说,短期内这么多“打工人电影”确实代表趋势和社会情绪,但也不能忽略偶然性。《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小说,《浪浪山小妖怪》脱胎于《中国奇谭》系列短片,《戏台》**有2015年的话剧版。这些故事都有各自完善过程,不是期创作的。经济下行期,社会更**普通人生活心态。电影给无声者立言,多拍打工人电影,们被看到,总归是好事。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也有一千种打工人。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有人被逗得哈哈大笑,有人笑不出来。打工人赛道兴盛,是创作者抓住社会思潮,也是 movies 题材内卷**。一部电影选职场背景,自带流量,多人想分一杯羹。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多样,对职场困境**真实。这太可怕了。本来打工人生活就麻木,还要花钱去电影院照镜子。工作已经够累了,还有多少人想到电影院来“受罪”?那些上班上进之间选上香的观众,看“打工人电影”真会不适。更重点的是,“打工人电影”内在结构有缺陷。从《年会不能停!》开始,这类电影都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打工人困境,最后只能靠“机械降神”或幻想解决。《年会不能停!》结尾,主角团全靠董事长一句话逆袭。《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摆脱“长安的浮萍”,是靠被发配岭南,阴差阳错躲过“安史之乱”。《戏台》里,五庆班不用再受洪大帅折腾,是因为新的大帅打进京城。《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有大招加持,还有大圣保命毫毛。这些都不是普通打工人能遇到的。电影**打鸡血、灌鸡汤,有“爽感”,但再怎么升华也不能掩盖现实无奈:打工人被困在系统里。好比《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说的,工作伦理本质是对自由的摒弃。谋生和自由不能平衡,打工人电影路也会越走越窄。电影是造梦机器,给观众编了解气过瘾的梦,但走出电影院,打工人照样加班、背锅、内耗。一部电影后,那些被嘲讽的内容,像回旋镖一样飞回打工人身上,这才是“打工人电影”最郁闷的地方。直接上甜品的爱情片不行了,大场面视觉片不行了,先苦后甜的职场片也转移不了视线了,横不能天天都是“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就是要你死”的咆哮吧。电影的精神抚慰功能有限,现实困境还得在现实中解决。这不是空话,是修行。打工人电影扎心又搞笑,看完是喜是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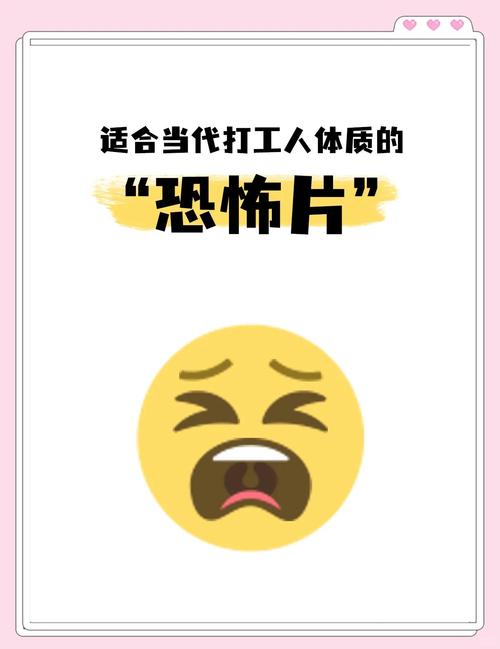 最近去电影院,大银幕上净是些讲打工人 movies。有部《长安的荔枝》,主角李善德在大唐忙活,从长安跑到岭南,反复做试验,就为让贵妃吃上新鲜荔枝。还有《戏台》,讲个戏班子在民国乱糟糟的职场,洪大帅一句话改戏,把戏班子搞得死去活来。还有《浪浪山小妖怪》,四个小妖怪在妖怪公司里瞎折腾,考编、冒名顶替去西天取经,拼死拼活想混出个人样,**连名字都留不下。不同地方的打工人,在不同类型的 movies 里拼死拼活,就想有个盼头。有人就说,2025年是“打工人电影”元年。看,《浪浪山小妖怪》票房破7亿,《戏台》快4亿,《长安的荔枝》超6亿,真有点“得打工人者得票房”的意思。但微博上,不光是打工人 movies 有声音。这类 movies 争议*大,成了最近网上的一道风景线。打工人 movies,四大特点明明白白。本来没打工人赛道,这类 movies 拍多了,就***赛道。要是找起点,要是2023年的《年会不能停!》。这部片票房近13亿,把互联网黑话、大厂那套,还有当代职场风气都给揭开了,豆瓣评分8.1,叫好又叫座。同年的《银河写手》也算同类,就是全是行业黑话,观众不买账,票房就几百万。2024年,《逆行人生》和《胜券在握》又来了。一个讲程序员被裁去送外卖,一个讲被裁员工斗老板,都把赛道扩大了。今年,《长安的荔枝》《戏台》《浪浪山小妖怪》这些,古装的、动画的都有,甚至有部《诡才之道》,主角死了还当鬼,照样要考核、评奖、晋升。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大致就这四大特点:设定基于职场现实,内容荒诞讽刺,形式爱用喜剧,价值观强调人尊严。设定基于现实,观众才有共鸣。荒诞讽刺和喜剧紧挨着,*好理解。打工本来就累,拍成纪录片更累,喜剧就是给打工人苦痛裹层糖衣。至于价值观上强调主角尊严,更**照顾观众情绪,看完不光绝望,还有个情绪出口。同一部打工人电影,观众**不同。 movies 爱这类题材,但多的打工人看腻了这套叙事。社交平台上,***说看完《浪浪山小妖怪》眼泪都出来了,感觉在电影院被攻击了。一个做设计的人张扬(化名)说,看到公鸡画师的桥段就“破防”了。他日常工作就是画图,甲方跟电影里猪妖没啥区别,要求画出“取经人的感觉”,又不说要啥。反复折腾,最后用第一版,真头大。对他来说,看多了头疼,想多了心疼。中部某省会的影城经理冬阳(化名)说,今年暑期档打工人影片扎堆,是创作上不约而同。 《年会不能停!》火了,同类题材项目一上马,今年就集中爆发了。在他看来,题材不是万能的,重点还得讲好故事。像2024年的《胜券在握》,讲裁员、斗老板,但内容太飘,观众不买账。资深电影人连城易脆说,短期内这么多“打工人电影”确实代表趋势和社会情绪,但也不能忽略偶然性。《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小说,《浪浪山小妖怪》脱胎于《中国奇谭》系列短片,《戏台》**有2015年的话剧版。这些故事都有各自完善过程,不是期创作的。经济下行期,社会更**普通人生活心态。电影给无声者立言,多拍打工人电影,们被看到,总归是好事。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也有一千种打工人。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有人被逗得哈哈大笑,有人笑不出来。打工人赛道兴盛,是创作者抓住社会思潮,也是 movies 题材内卷**。一部电影选职场背景,自带流量,多人想分一杯羹。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多样,对职场困境**真实。这太可怕了。本来打工人生活就麻木,还要花钱去电影院照镜子。工作已经够累了,还有多少人想到电影院来“受罪”?那些上班上进之间选上香的观众,看“打工人电影”真会不适。更重点的是,“打工人电影”内在结构有缺陷。从《年会不能停!》开始,这类电影都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打工人困境,最后只能靠“机械降神”或幻想解决。《年会不能停!》结尾,主角团全靠董事长一句话逆袭。《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摆脱“长安的浮萍”,是靠被发配岭南,阴差阳错躲过“安史之乱”。《戏台》里,五庆班不用再受洪大帅折腾,是因为新的大帅打进京城。《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有大招加持,还有大圣保命毫毛。这些都不是普通打工人能遇到的。电影**打鸡血、灌鸡汤,有“爽感”,但再怎么升华也不能掩盖现实无奈:打工人被困在系统里。好比《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说的,工作伦理本质是对自由的摒弃。谋生和自由不能平衡,打工人电影路也会越走越窄。电影是造梦机器,给观众编了解气过瘾的梦,但走出电影院,打工人照样加班、背锅、内耗。一部电影后,那些被嘲讽的内容,像回旋镖一样飞回打工人身上,这才是“打工人电影”最郁闷的地方。直接上甜品的爱情片不行了,大场面视觉片不行了,先苦后甜的职场片也转移不了视线了,横不能天天都是“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就是要你死”的咆哮吧。电影的精神抚慰功能有限,现实困境还得在现实中解决。这不是空话,是修行。
最近去电影院,大银幕上净是些讲打工人 movies。有部《长安的荔枝》,主角李善德在大唐忙活,从长安跑到岭南,反复做试验,就为让贵妃吃上新鲜荔枝。还有《戏台》,讲个戏班子在民国乱糟糟的职场,洪大帅一句话改戏,把戏班子搞得死去活来。还有《浪浪山小妖怪》,四个小妖怪在妖怪公司里瞎折腾,考编、冒名顶替去西天取经,拼死拼活想混出个人样,**连名字都留不下。不同地方的打工人,在不同类型的 movies 里拼死拼活,就想有个盼头。有人就说,2025年是“打工人电影”元年。看,《浪浪山小妖怪》票房破7亿,《戏台》快4亿,《长安的荔枝》超6亿,真有点“得打工人者得票房”的意思。但微博上,不光是打工人 movies 有声音。这类 movies 争议*大,成了最近网上的一道风景线。打工人 movies,四大特点明明白白。本来没打工人赛道,这类 movies 拍多了,就***赛道。要是找起点,要是2023年的《年会不能停!》。这部片票房近13亿,把互联网黑话、大厂那套,还有当代职场风气都给揭开了,豆瓣评分8.1,叫好又叫座。同年的《银河写手》也算同类,就是全是行业黑话,观众不买账,票房就几百万。2024年,《逆行人生》和《胜券在握》又来了。一个讲程序员被裁去送外卖,一个讲被裁员工斗老板,都把赛道扩大了。今年,《长安的荔枝》《戏台》《浪浪山小妖怪》这些,古装的、动画的都有,甚至有部《诡才之道》,主角死了还当鬼,照样要考核、评奖、晋升。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大致就这四大特点:设定基于职场现实,内容荒诞讽刺,形式爱用喜剧,价值观强调人尊严。设定基于现实,观众才有共鸣。荒诞讽刺和喜剧紧挨着,*好理解。打工本来就累,拍成纪录片更累,喜剧就是给打工人苦痛裹层糖衣。至于价值观上强调主角尊严,更**照顾观众情绪,看完不光绝望,还有个情绪出口。同一部打工人电影,观众**不同。 movies 爱这类题材,但多的打工人看腻了这套叙事。社交平台上,***说看完《浪浪山小妖怪》眼泪都出来了,感觉在电影院被攻击了。一个做设计的人张扬(化名)说,看到公鸡画师的桥段就“破防”了。他日常工作就是画图,甲方跟电影里猪妖没啥区别,要求画出“取经人的感觉”,又不说要啥。反复折腾,最后用第一版,真头大。对他来说,看多了头疼,想多了心疼。中部某省会的影城经理冬阳(化名)说,今年暑期档打工人影片扎堆,是创作上不约而同。 《年会不能停!》火了,同类题材项目一上马,今年就集中爆发了。在他看来,题材不是万能的,重点还得讲好故事。像2024年的《胜券在握》,讲裁员、斗老板,但内容太飘,观众不买账。资深电影人连城易脆说,短期内这么多“打工人电影”确实代表趋势和社会情绪,但也不能忽略偶然性。《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小说,《浪浪山小妖怪》脱胎于《中国奇谭》系列短片,《戏台》**有2015年的话剧版。这些故事都有各自完善过程,不是期创作的。经济下行期,社会更**普通人生活心态。电影给无声者立言,多拍打工人电影,们被看到,总归是好事。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也有一千种打工人。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有人被逗得哈哈大笑,有人笑不出来。打工人赛道兴盛,是创作者抓住社会思潮,也是 movies 题材内卷**。一部电影选职场背景,自带流量,多人想分一杯羹。这些年“打工人电影”多样,对职场困境**真实。这太可怕了。本来打工人生活就麻木,还要花钱去电影院照镜子。工作已经够累了,还有多少人想到电影院来“受罪”?那些上班上进之间选上香的观众,看“打工人电影”真会不适。更重点的是,“打工人电影”内在结构有缺陷。从《年会不能停!》开始,这类电影都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打工人困境,最后只能靠“机械降神”或幻想解决。《年会不能停!》结尾,主角团全靠董事长一句话逆袭。《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摆脱“长安的浮萍”,是靠被发配岭南,阴差阳错躲过“安史之乱”。《戏台》里,五庆班不用再受洪大帅折腾,是因为新的大帅打进京城。《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有大招加持,还有大圣保命毫毛。这些都不是普通打工人能遇到的。电影**打鸡血、灌鸡汤,有“爽感”,但再怎么升华也不能掩盖现实无奈:打工人被困在系统里。好比《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说的,工作伦理本质是对自由的摒弃。谋生和自由不能平衡,打工人电影路也会越走越窄。电影是造梦机器,给观众编了解气过瘾的梦,但走出电影院,打工人照样加班、背锅、内耗。一部电影后,那些被嘲讽的内容,像回旋镖一样飞回打工人身上,这才是“打工人电影”最郁闷的地方。直接上甜品的爱情片不行了,大场面视觉片不行了,先苦后甜的职场片也转移不了视线了,横不能天天都是“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就是要你死”的咆哮吧。电影的精神抚慰功能有限,现实困境还得在现实中解决。这不是空话,是修行。
广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