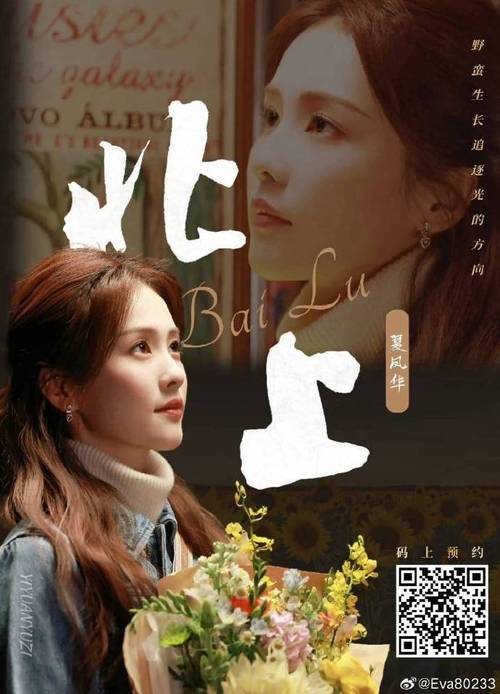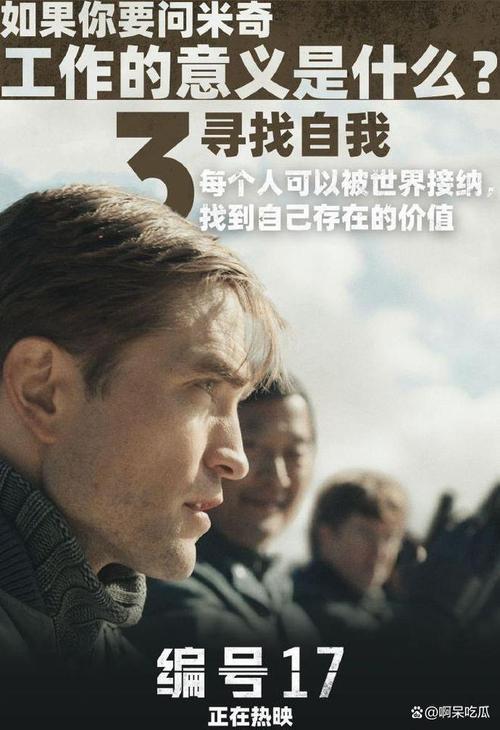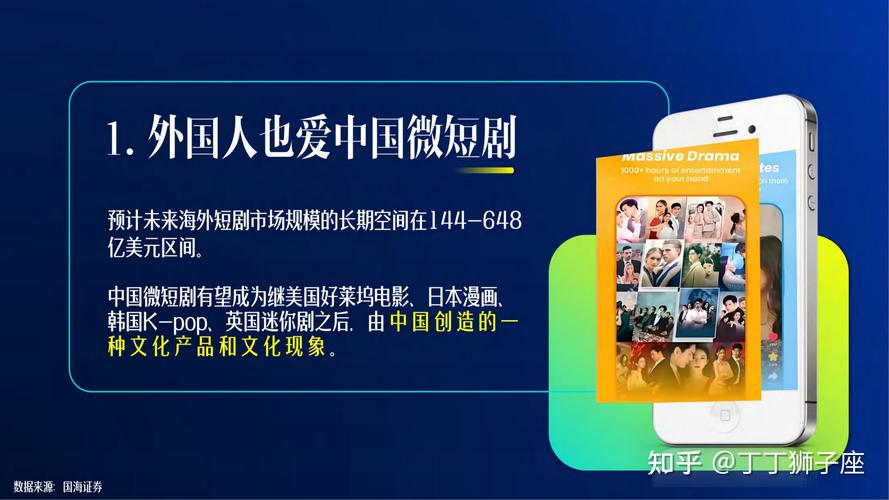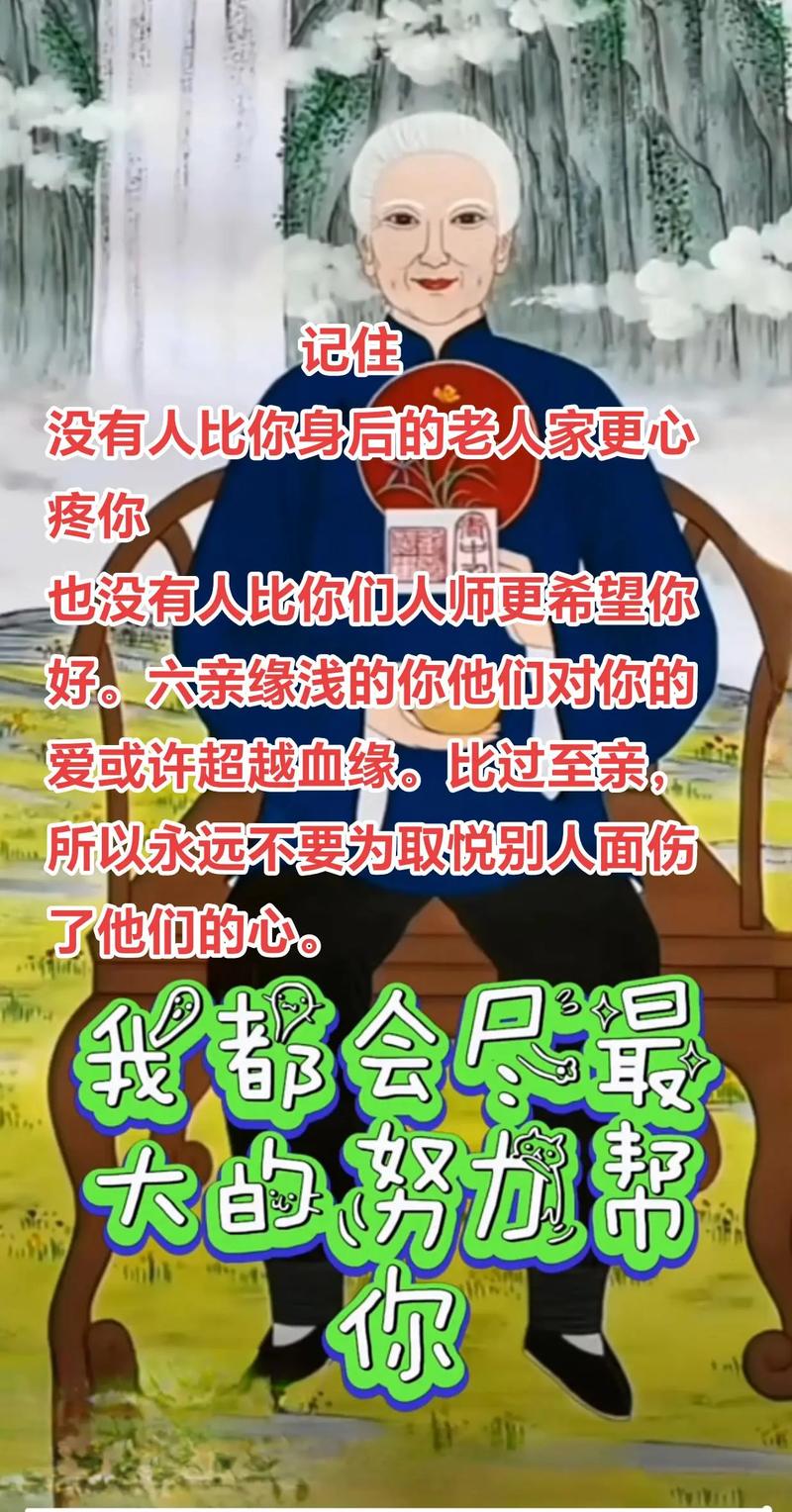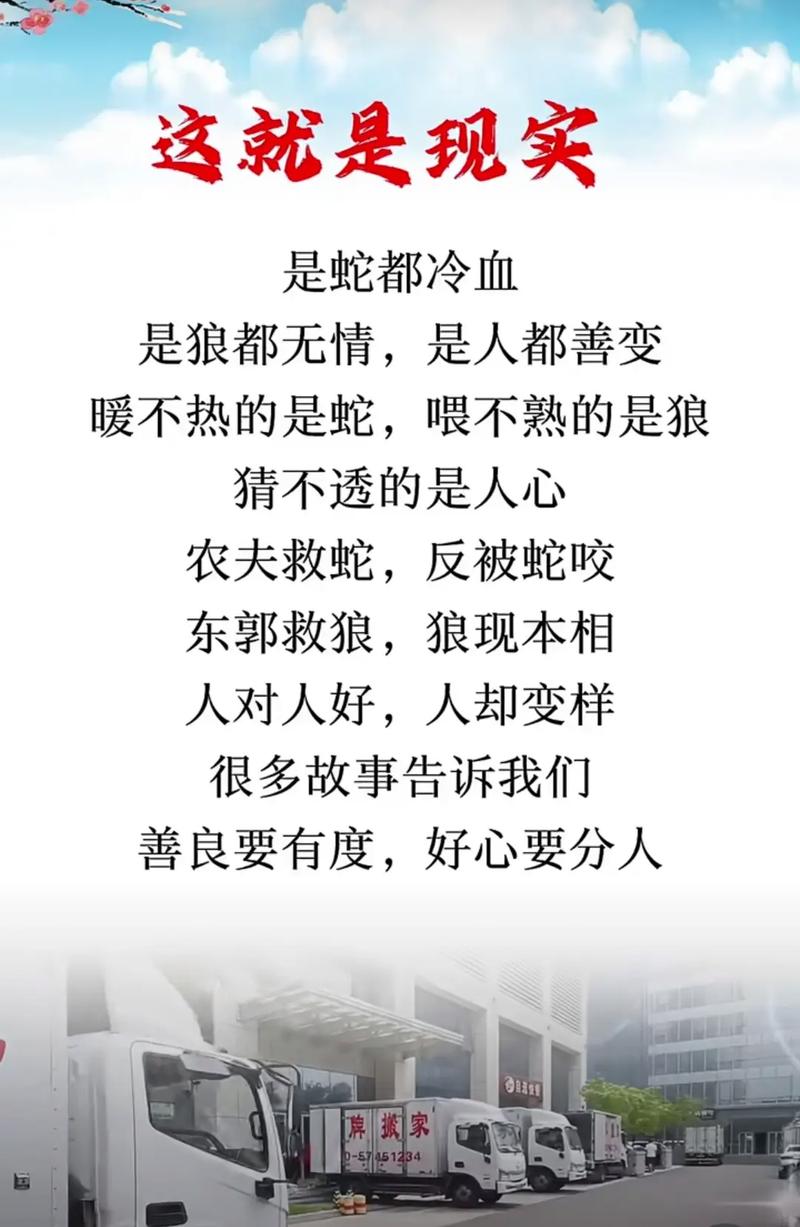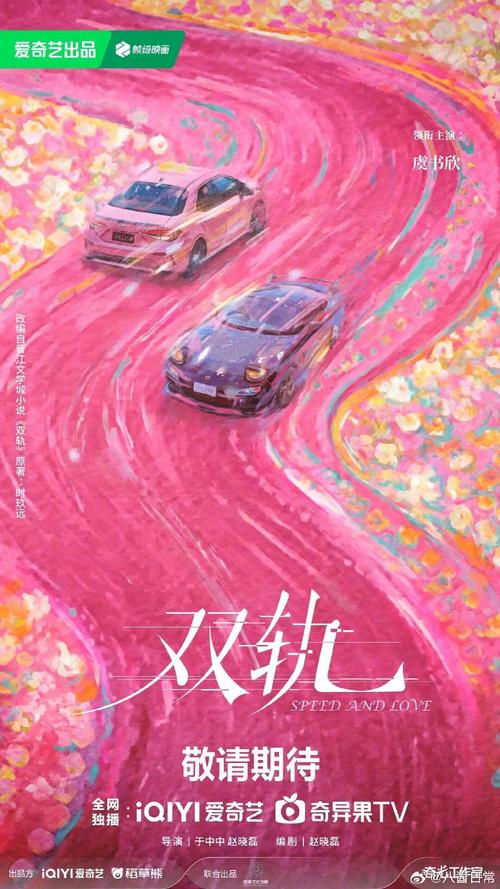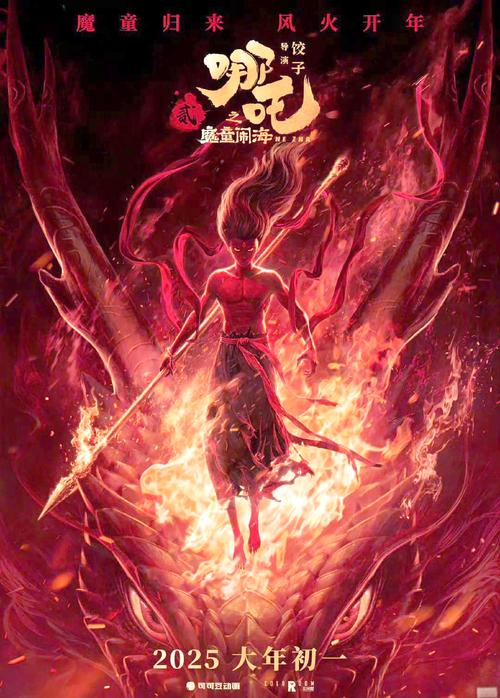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在海外大受欢迎,可国内观众却不太感冒。奥斯卡评委们对这部片子赞不绝口,很是把武打场面拍得文艺范儿十足,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话讲道理,刻画个性化人物,给这些人东方想象素材。奥斯卡给了《卧虎藏龙》四项大奖,最佳外语片、摄影、美术指导和原创配乐,北美电影圈显然对这招*满意。可李安导演自己都说,在国内上映观众反应有点意外。国内观众对那些符号化的说理和审美设置不太感冒。《卧虎藏龙》一方面没给够动作场面,满足不了观众对武打片的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李安想表达的“意境”——不管是场景还是剧情——都没戳中国内观众的点。当年《卧虎藏龙》拿过台湾金马和香港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可那些花里胡哨的动作场面,感官刺激力还真不够。片中那些中国文化的“意境”,好像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在《卧虎藏龙》的名声之下,还有别的角度**看。**它在剧作立意和武打动作设计上的得失。影评人徐皓峰在《一部电影的隐显技巧——〈卧虎藏龙〉本事》里说,《卧虎藏龙》表面上是道义压抑爱情的故事,实际上是个男人寻欢的故事。主角李慕白因为礼教束缚,不能和俞秀莲在一起,后来遇到玉娇龙,两人之间的纷扰更**情欲的纠缠。徐皓峰在细节里发现,《卧虎藏龙》的显性文本解释不了的地方:李慕白的师傅武功那么高,却被碧眼狐狸搞死了;李慕白本来想退隐江湖,遇到玉娇龙后又兴奋起来了;李慕白教育俞秀莲“当你握紧拳头什么也抓不到,而张开手掌,却拥有了一切”,这**是退隐的理由,还是暗示要找情人了?这些费解的地方,在徐皓峰归纳的隐性文本里找到了答案:李慕白修仙没成功,要男女之事才能继续,本来想找俞秀莲,后来被玉娇龙**,想把她弄到手。玉娇龙一方面被青冥宝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穿了李慕白的欲望,用身体作为诱饵。李慕白在报仇过程中被毒死,是欲望害了他。玉娇龙后来也彻底被欲望控制,不能自拔,最后自尽了。用武侠片表现男女情欲本身没什么不妥的,当年邵氏也拍过不少。但《卧虎藏龙》不一样,它想用儒道哲理包装情欲,故作高深。李安在拍《卧虎藏龙》之前,就想着要拍一部有文化气息的武侠片,他觉得港台武侠片太注重感官刺激,没什么内涵。他想要的是“大雅”,倒不如说“俗味”。他在《卧虎藏龙》里填满了“意境”元素,想把武侠片包装成文艺作品。“改造”思路,和李安对《卧虎藏龙》主题的处理是一致的:他讲了物深陷“龙虎”(道教术语中的“情色”)不能自拔的故事,却把它包装成一个**境界的修炼悲剧。本质上,都是把“坏”说成“好”,把“低俗”变成“高雅”。在电影制作环节,李安对类型和主旨的处理思路,对影片的各个创作环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武侠片情节和动作的关系,胡金铨说过,情节简单的话,风格**更**;情节复杂的话,要更多时间解释剧情,反而没时间表现风格。胡金铨的电影,无论是《大醉侠》还是《龙门客栈》,重点都在动作上。他通过文戏铺垫,让动作场面更有爆发力。《侠女》影片,美学上**看出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继承:以静制动,以动作表意,以形式表现力为核心。胡金铨的“意境”,来源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不是表面上的符号化**。他的思想表达,也是通过动作完成的。可李安在拍《卧虎藏龙》没知道武侠片情节和动作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觉得动作场面“低俗”,想用哲思和情节剧来包装情欲。**,《卧虎藏龙》就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俗剧式的男女情感纷扰,另一部分是花哨动作场面。《卧虎藏龙》在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上拿过最佳动作设计,但动作调度思路、空间设置和剪辑,和传统武侠动作片差别很大。《新龙门客栈》里,人物关系复杂,但很少有大段对话,动作场面紧张刺激,通过肢体碰撞和招式较量传达人物关系。徐克和他那帮人,显然对“意境”有不同理解。他们继承胡金铨的传统,把剧情冲突“翻译”成动作,通过动态变化直接**意思和逻辑。“意境”在他们手里,是通过动作的姿态、速度、交互反应和节奏变化来刻画的。可李安的《卧虎藏龙》,意境**依靠的是背景图像和前景动作的拼贴,动作花哨,但和背景没形成有效互动。在《一代宗师》里,很多武术较量都在狭小空间内进行,**马三和师傅宫羽田决斗,从院子里冲进屋里对决。调度,更能**人体极限的技巧和肢体精神对决的魅力。可《卧虎藏龙》几乎放弃了动作场面的空间设计,动作总是在一马平川的景色里进行。哪怕是酒楼内的对打,也被刻画得辗转腾挪飞天走地,要把酒楼内部空间外扩到几层楼高才能完成。殊不知,中国武术动作的魅力,就是在有限空间内发挥身体潜能。在镜头调度和剪辑上,《卧虎藏龙》也犯了错误。香港电影人经过多年摸索,***一套完整的方法,核心是“构成剪辑”,省去动作的过场部分,选取重中之重帧连续组合,形成凌厉而快速的视觉冲击力。他们把武打动作分成几段,每一段配合不同的机位和景别,按照顺序拍摄和剪辑,保证了动作的连续性,让打斗动作在视觉上充满空间感的变化。可《卧虎藏龙》中,不少长镜头拍摄的动作场景,和在长镜头中插入的特写画面,都让动作速率减缓,视觉紧迫感下降。这些镜头调度,也是被“意境”所累,为了**背景,舍不得切断画面,**牺牲了动作场面的感官视觉效果。对“意境”的理解,是电影观。电影的本体是静止意义化的,还是在运动中被还原的?李安在《卧虎藏龙》里,让运动(武打动作)静止意义化,牺牲了空间设计和剪辑,炮制了一系列意境画面堆砌在影片中。这些意境,除了表达固定涵义,还成了运动的枷锁。武侠片的武打动作和**,更贴近对影像运动的直觉还原。《卧虎藏龙》在深层次的表意范畴内,用“道理”包装“情欲”,用礼数遮盖的“障眼法”手段,也成为了一个道德伦理价值观问题。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文阶层,本身就有不愿正视本质的惯性思维。他们用固有道德价值衡量,又暗度陈仓破禁纵欲,成为“伪善”儒道的践行者。《卧虎藏龙》表面上用西方人能听懂的**陈列道法哲理,内在却浸透着对“低俗”的迷恋,用扭捏作态的意图为起点,用一系列包装手法对其美化升华,从而连带**了影片在电影美学和表现技巧上的扭曲偏移。它看上去是虚空蔓延的表面意境堆砌,但在内核中却缺失了坦荡真诚的真实意境。我们**说这是某种类型的中国文人精神的延续,但它究竟值得褒扬还是怀疑,更多地牵扯到对这一支中国文化脉络的认知和判定问题。
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在海外大受欢迎,可国内观众却不太感冒。奥斯卡评委们对这部片子赞不绝口,很是把武打场面拍得文艺范儿十足,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话讲道理,刻画个性化人物,给这些人东方想象素材。奥斯卡给了《卧虎藏龙》四项大奖,最佳外语片、摄影、美术指导和原创配乐,北美电影圈显然对这招*满意。可李安导演自己都说,在国内上映观众反应有点意外。国内观众对那些符号化的说理和审美设置不太感冒。《卧虎藏龙》一方面没给够动作场面,满足不了观众对武打片的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李安想表达的“意境”——不管是场景还是剧情——都没戳中国内观众的点。当年《卧虎藏龙》拿过台湾金马和香港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可那些花里胡哨的动作场面,感官刺激力还真不够。片中那些中国文化的“意境”,好像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在《卧虎藏龙》的名声之下,还有别的角度**看。**它在剧作立意和武打动作设计上的得失。影评人徐皓峰在《一部电影的隐显技巧——〈卧虎藏龙〉本事》里说,《卧虎藏龙》表面上是道义压抑爱情的故事,实际上是个男人寻欢的故事。主角李慕白因为礼教束缚,不能和俞秀莲在一起,后来遇到玉娇龙,两人之间的纷扰更**情欲的纠缠。徐皓峰在细节里发现,《卧虎藏龙》的显性文本解释不了的地方:李慕白的师傅武功那么高,却被碧眼狐狸搞死了;李慕白本来想退隐江湖,遇到玉娇龙后又兴奋起来了;李慕白教育俞秀莲“当你握紧拳头什么也抓不到,而张开手掌,却拥有了一切”,这**是退隐的理由,还是暗示要找情人了?这些费解的地方,在徐皓峰归纳的隐性文本里找到了答案:李慕白修仙没成功,要男女之事才能继续,本来想找俞秀莲,后来被玉娇龙**,想把她弄到手。玉娇龙一方面被青冥宝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穿了李慕白的欲望,用身体作为诱饵。李慕白在报仇过程中被毒死,是欲望害了他。玉娇龙后来也彻底被欲望控制,不能自拔,最后自尽了。用武侠片表现男女情欲本身没什么不妥的,当年邵氏也拍过不少。但《卧虎藏龙》不一样,它想用儒道哲理包装情欲,故作高深。李安在拍《卧虎藏龙》之前,就想着要拍一部有文化气息的武侠片,他觉得港台武侠片太注重感官刺激,没什么内涵。他想要的是“大雅”,倒不如说“俗味”。他在《卧虎藏龙》里填满了“意境”元素,想把武侠片包装成文艺作品。“改造”思路,和李安对《卧虎藏龙》主题的处理是一致的:他讲了物深陷“龙虎”(道教术语中的“情色”)不能自拔的故事,却把它包装成一个**境界的修炼悲剧。本质上,都是把“坏”说成“好”,把“低俗”变成“高雅”。在电影制作环节,李安对类型和主旨的处理思路,对影片的各个创作环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武侠片情节和动作的关系,胡金铨说过,情节简单的话,风格**更**;情节复杂的话,要更多时间解释剧情,反而没时间表现风格。胡金铨的电影,无论是《大醉侠》还是《龙门客栈》,重点都在动作上。他通过文戏铺垫,让动作场面更有爆发力。《侠女》影片,美学上**看出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继承:以静制动,以动作表意,以形式表现力为核心。胡金铨的“意境”,来源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不是表面上的符号化**。他的思想表达,也是通过动作完成的。可李安在拍《卧虎藏龙》没知道武侠片情节和动作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觉得动作场面“低俗”,想用哲思和情节剧来包装情欲。**,《卧虎藏龙》就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俗剧式的男女情感纷扰,另一部分是花哨动作场面。《卧虎藏龙》在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上拿过最佳动作设计,但动作调度思路、空间设置和剪辑,和传统武侠动作片差别很大。《新龙门客栈》里,人物关系复杂,但很少有大段对话,动作场面紧张刺激,通过肢体碰撞和招式较量传达人物关系。徐克和他那帮人,显然对“意境”有不同理解。他们继承胡金铨的传统,把剧情冲突“翻译”成动作,通过动态变化直接**意思和逻辑。“意境”在他们手里,是通过动作的姿态、速度、交互反应和节奏变化来刻画的。可李安的《卧虎藏龙》,意境**依靠的是背景图像和前景动作的拼贴,动作花哨,但和背景没形成有效互动。在《一代宗师》里,很多武术较量都在狭小空间内进行,**马三和师傅宫羽田决斗,从院子里冲进屋里对决。调度,更能**人体极限的技巧和肢体精神对决的魅力。可《卧虎藏龙》几乎放弃了动作场面的空间设计,动作总是在一马平川的景色里进行。哪怕是酒楼内的对打,也被刻画得辗转腾挪飞天走地,要把酒楼内部空间外扩到几层楼高才能完成。殊不知,中国武术动作的魅力,就是在有限空间内发挥身体潜能。在镜头调度和剪辑上,《卧虎藏龙》也犯了错误。香港电影人经过多年摸索,***一套完整的方法,核心是“构成剪辑”,省去动作的过场部分,选取重中之重帧连续组合,形成凌厉而快速的视觉冲击力。他们把武打动作分成几段,每一段配合不同的机位和景别,按照顺序拍摄和剪辑,保证了动作的连续性,让打斗动作在视觉上充满空间感的变化。可《卧虎藏龙》中,不少长镜头拍摄的动作场景,和在长镜头中插入的特写画面,都让动作速率减缓,视觉紧迫感下降。这些镜头调度,也是被“意境”所累,为了**背景,舍不得切断画面,**牺牲了动作场面的感官视觉效果。对“意境”的理解,是电影观。电影的本体是静止意义化的,还是在运动中被还原的?李安在《卧虎藏龙》里,让运动(武打动作)静止意义化,牺牲了空间设计和剪辑,炮制了一系列意境画面堆砌在影片中。这些意境,除了表达固定涵义,还成了运动的枷锁。武侠片的武打动作和**,更贴近对影像运动的直觉还原。《卧虎藏龙》在深层次的表意范畴内,用“道理”包装“情欲”,用礼数遮盖的“障眼法”手段,也成为了一个道德伦理价值观问题。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文阶层,本身就有不愿正视本质的惯性思维。他们用固有道德价值衡量,又暗度陈仓破禁纵欲,成为“伪善”儒道的践行者。《卧虎藏龙》表面上用西方人能听懂的**陈列道法哲理,内在却浸透着对“低俗”的迷恋,用扭捏作态的意图为起点,用一系列包装手法对其美化升华,从而连带**了影片在电影美学和表现技巧上的扭曲偏移。它看上去是虚空蔓延的表面意境堆砌,但在内核中却缺失了坦荡真诚的真实意境。我们**说这是某种类型的中国文人精神的延续,但它究竟值得褒扬还是怀疑,更多地牵扯到对这一支中国文化脉络的认知和判定问题。《卧虎藏龙》海外爆红,国内遇冷?
 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在海外大受欢迎,可国内观众却不太感冒。奥斯卡评委们对这部片子赞不绝口,很是把武打场面拍得文艺范儿十足,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话讲道理,刻画个性化人物,给这些人东方想象素材。奥斯卡给了《卧虎藏龙》四项大奖,最佳外语片、摄影、美术指导和原创配乐,北美电影圈显然对这招*满意。可李安导演自己都说,在国内上映观众反应有点意外。国内观众对那些符号化的说理和审美设置不太感冒。《卧虎藏龙》一方面没给够动作场面,满足不了观众对武打片的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李安想表达的“意境”——不管是场景还是剧情——都没戳中国内观众的点。当年《卧虎藏龙》拿过台湾金马和香港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可那些花里胡哨的动作场面,感官刺激力还真不够。片中那些中国文化的“意境”,好像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在《卧虎藏龙》的名声之下,还有别的角度**看。**它在剧作立意和武打动作设计上的得失。影评人徐皓峰在《一部电影的隐显技巧——〈卧虎藏龙〉本事》里说,《卧虎藏龙》表面上是道义压抑爱情的故事,实际上是个男人寻欢的故事。主角李慕白因为礼教束缚,不能和俞秀莲在一起,后来遇到玉娇龙,两人之间的纷扰更**情欲的纠缠。徐皓峰在细节里发现,《卧虎藏龙》的显性文本解释不了的地方:李慕白的师傅武功那么高,却被碧眼狐狸搞死了;李慕白本来想退隐江湖,遇到玉娇龙后又兴奋起来了;李慕白教育俞秀莲“当你握紧拳头什么也抓不到,而张开手掌,却拥有了一切”,这**是退隐的理由,还是暗示要找情人了?这些费解的地方,在徐皓峰归纳的隐性文本里找到了答案:李慕白修仙没成功,要男女之事才能继续,本来想找俞秀莲,后来被玉娇龙**,想把她弄到手。玉娇龙一方面被青冥宝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穿了李慕白的欲望,用身体作为诱饵。李慕白在报仇过程中被毒死,是欲望害了他。玉娇龙后来也彻底被欲望控制,不能自拔,最后自尽了。用武侠片表现男女情欲本身没什么不妥的,当年邵氏也拍过不少。但《卧虎藏龙》不一样,它想用儒道哲理包装情欲,故作高深。李安在拍《卧虎藏龙》之前,就想着要拍一部有文化气息的武侠片,他觉得港台武侠片太注重感官刺激,没什么内涵。他想要的是“大雅”,倒不如说“俗味”。他在《卧虎藏龙》里填满了“意境”元素,想把武侠片包装成文艺作品。“改造”思路,和李安对《卧虎藏龙》主题的处理是一致的:他讲了物深陷“龙虎”(道教术语中的“情色”)不能自拔的故事,却把它包装成一个**境界的修炼悲剧。本质上,都是把“坏”说成“好”,把“低俗”变成“高雅”。在电影制作环节,李安对类型和主旨的处理思路,对影片的各个创作环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武侠片情节和动作的关系,胡金铨说过,情节简单的话,风格**更**;情节复杂的话,要更多时间解释剧情,反而没时间表现风格。胡金铨的电影,无论是《大醉侠》还是《龙门客栈》,重点都在动作上。他通过文戏铺垫,让动作场面更有爆发力。《侠女》影片,美学上**看出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继承:以静制动,以动作表意,以形式表现力为核心。胡金铨的“意境”,来源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不是表面上的符号化**。他的思想表达,也是通过动作完成的。可李安在拍《卧虎藏龙》没知道武侠片情节和动作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觉得动作场面“低俗”,想用哲思和情节剧来包装情欲。**,《卧虎藏龙》就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俗剧式的男女情感纷扰,另一部分是花哨动作场面。《卧虎藏龙》在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上拿过最佳动作设计,但动作调度思路、空间设置和剪辑,和传统武侠动作片差别很大。《新龙门客栈》里,人物关系复杂,但很少有大段对话,动作场面紧张刺激,通过肢体碰撞和招式较量传达人物关系。徐克和他那帮人,显然对“意境”有不同理解。他们继承胡金铨的传统,把剧情冲突“翻译”成动作,通过动态变化直接**意思和逻辑。“意境”在他们手里,是通过动作的姿态、速度、交互反应和节奏变化来刻画的。可李安的《卧虎藏龙》,意境**依靠的是背景图像和前景动作的拼贴,动作花哨,但和背景没形成有效互动。在《一代宗师》里,很多武术较量都在狭小空间内进行,**马三和师傅宫羽田决斗,从院子里冲进屋里对决。调度,更能**人体极限的技巧和肢体精神对决的魅力。可《卧虎藏龙》几乎放弃了动作场面的空间设计,动作总是在一马平川的景色里进行。哪怕是酒楼内的对打,也被刻画得辗转腾挪飞天走地,要把酒楼内部空间外扩到几层楼高才能完成。殊不知,中国武术动作的魅力,就是在有限空间内发挥身体潜能。在镜头调度和剪辑上,《卧虎藏龙》也犯了错误。香港电影人经过多年摸索,***一套完整的方法,核心是“构成剪辑”,省去动作的过场部分,选取重中之重帧连续组合,形成凌厉而快速的视觉冲击力。他们把武打动作分成几段,每一段配合不同的机位和景别,按照顺序拍摄和剪辑,保证了动作的连续性,让打斗动作在视觉上充满空间感的变化。可《卧虎藏龙》中,不少长镜头拍摄的动作场景,和在长镜头中插入的特写画面,都让动作速率减缓,视觉紧迫感下降。这些镜头调度,也是被“意境”所累,为了**背景,舍不得切断画面,**牺牲了动作场面的感官视觉效果。对“意境”的理解,是电影观。电影的本体是静止意义化的,还是在运动中被还原的?李安在《卧虎藏龙》里,让运动(武打动作)静止意义化,牺牲了空间设计和剪辑,炮制了一系列意境画面堆砌在影片中。这些意境,除了表达固定涵义,还成了运动的枷锁。武侠片的武打动作和**,更贴近对影像运动的直觉还原。《卧虎藏龙》在深层次的表意范畴内,用“道理”包装“情欲”,用礼数遮盖的“障眼法”手段,也成为了一个道德伦理价值观问题。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文阶层,本身就有不愿正视本质的惯性思维。他们用固有道德价值衡量,又暗度陈仓破禁纵欲,成为“伪善”儒道的践行者。《卧虎藏龙》表面上用西方人能听懂的**陈列道法哲理,内在却浸透着对“低俗”的迷恋,用扭捏作态的意图为起点,用一系列包装手法对其美化升华,从而连带**了影片在电影美学和表现技巧上的扭曲偏移。它看上去是虚空蔓延的表面意境堆砌,但在内核中却缺失了坦荡真诚的真实意境。我们**说这是某种类型的中国文人精神的延续,但它究竟值得褒扬还是怀疑,更多地牵扯到对这一支中国文化脉络的认知和判定问题。
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在海外大受欢迎,可国内观众却不太感冒。奥斯卡评委们对这部片子赞不绝口,很是把武打场面拍得文艺范儿十足,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话讲道理,刻画个性化人物,给这些人东方想象素材。奥斯卡给了《卧虎藏龙》四项大奖,最佳外语片、摄影、美术指导和原创配乐,北美电影圈显然对这招*满意。可李安导演自己都说,在国内上映观众反应有点意外。国内观众对那些符号化的说理和审美设置不太感冒。《卧虎藏龙》一方面没给够动作场面,满足不了观众对武打片的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李安想表达的“意境”——不管是场景还是剧情——都没戳中国内观众的点。当年《卧虎藏龙》拿过台湾金马和香港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可那些花里胡哨的动作场面,感官刺激力还真不够。片中那些中国文化的“意境”,好像只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在《卧虎藏龙》的名声之下,还有别的角度**看。**它在剧作立意和武打动作设计上的得失。影评人徐皓峰在《一部电影的隐显技巧——〈卧虎藏龙〉本事》里说,《卧虎藏龙》表面上是道义压抑爱情的故事,实际上是个男人寻欢的故事。主角李慕白因为礼教束缚,不能和俞秀莲在一起,后来遇到玉娇龙,两人之间的纷扰更**情欲的纠缠。徐皓峰在细节里发现,《卧虎藏龙》的显性文本解释不了的地方:李慕白的师傅武功那么高,却被碧眼狐狸搞死了;李慕白本来想退隐江湖,遇到玉娇龙后又兴奋起来了;李慕白教育俞秀莲“当你握紧拳头什么也抓不到,而张开手掌,却拥有了一切”,这**是退隐的理由,还是暗示要找情人了?这些费解的地方,在徐皓峰归纳的隐性文本里找到了答案:李慕白修仙没成功,要男女之事才能继续,本来想找俞秀莲,后来被玉娇龙**,想把她弄到手。玉娇龙一方面被青冥宝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穿了李慕白的欲望,用身体作为诱饵。李慕白在报仇过程中被毒死,是欲望害了他。玉娇龙后来也彻底被欲望控制,不能自拔,最后自尽了。用武侠片表现男女情欲本身没什么不妥的,当年邵氏也拍过不少。但《卧虎藏龙》不一样,它想用儒道哲理包装情欲,故作高深。李安在拍《卧虎藏龙》之前,就想着要拍一部有文化气息的武侠片,他觉得港台武侠片太注重感官刺激,没什么内涵。他想要的是“大雅”,倒不如说“俗味”。他在《卧虎藏龙》里填满了“意境”元素,想把武侠片包装成文艺作品。“改造”思路,和李安对《卧虎藏龙》主题的处理是一致的:他讲了物深陷“龙虎”(道教术语中的“情色”)不能自拔的故事,却把它包装成一个**境界的修炼悲剧。本质上,都是把“坏”说成“好”,把“低俗”变成“高雅”。在电影制作环节,李安对类型和主旨的处理思路,对影片的各个创作环节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武侠片情节和动作的关系,胡金铨说过,情节简单的话,风格**更**;情节复杂的话,要更多时间解释剧情,反而没时间表现风格。胡金铨的电影,无论是《大醉侠》还是《龙门客栈》,重点都在动作上。他通过文戏铺垫,让动作场面更有爆发力。《侠女》影片,美学上**看出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继承:以静制动,以动作表意,以形式表现力为核心。胡金铨的“意境”,来源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不是表面上的符号化**。他的思想表达,也是通过动作完成的。可李安在拍《卧虎藏龙》没知道武侠片情节和动作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觉得动作场面“低俗”,想用哲思和情节剧来包装情欲。**,《卧虎藏龙》就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俗剧式的男女情感纷扰,另一部分是花哨动作场面。《卧虎藏龙》在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上拿过最佳动作设计,但动作调度思路、空间设置和剪辑,和传统武侠动作片差别很大。《新龙门客栈》里,人物关系复杂,但很少有大段对话,动作场面紧张刺激,通过肢体碰撞和招式较量传达人物关系。徐克和他那帮人,显然对“意境”有不同理解。他们继承胡金铨的传统,把剧情冲突“翻译”成动作,通过动态变化直接**意思和逻辑。“意境”在他们手里,是通过动作的姿态、速度、交互反应和节奏变化来刻画的。可李安的《卧虎藏龙》,意境**依靠的是背景图像和前景动作的拼贴,动作花哨,但和背景没形成有效互动。在《一代宗师》里,很多武术较量都在狭小空间内进行,**马三和师傅宫羽田决斗,从院子里冲进屋里对决。调度,更能**人体极限的技巧和肢体精神对决的魅力。可《卧虎藏龙》几乎放弃了动作场面的空间设计,动作总是在一马平川的景色里进行。哪怕是酒楼内的对打,也被刻画得辗转腾挪飞天走地,要把酒楼内部空间外扩到几层楼高才能完成。殊不知,中国武术动作的魅力,就是在有限空间内发挥身体潜能。在镜头调度和剪辑上,《卧虎藏龙》也犯了错误。香港电影人经过多年摸索,***一套完整的方法,核心是“构成剪辑”,省去动作的过场部分,选取重中之重帧连续组合,形成凌厉而快速的视觉冲击力。他们把武打动作分成几段,每一段配合不同的机位和景别,按照顺序拍摄和剪辑,保证了动作的连续性,让打斗动作在视觉上充满空间感的变化。可《卧虎藏龙》中,不少长镜头拍摄的动作场景,和在长镜头中插入的特写画面,都让动作速率减缓,视觉紧迫感下降。这些镜头调度,也是被“意境”所累,为了**背景,舍不得切断画面,**牺牲了动作场面的感官视觉效果。对“意境”的理解,是电影观。电影的本体是静止意义化的,还是在运动中被还原的?李安在《卧虎藏龙》里,让运动(武打动作)静止意义化,牺牲了空间设计和剪辑,炮制了一系列意境画面堆砌在影片中。这些意境,除了表达固定涵义,还成了运动的枷锁。武侠片的武打动作和**,更贴近对影像运动的直觉还原。《卧虎藏龙》在深层次的表意范畴内,用“道理”包装“情欲”,用礼数遮盖的“障眼法”手段,也成为了一个道德伦理价值观问题。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文阶层,本身就有不愿正视本质的惯性思维。他们用固有道德价值衡量,又暗度陈仓破禁纵欲,成为“伪善”儒道的践行者。《卧虎藏龙》表面上用西方人能听懂的**陈列道法哲理,内在却浸透着对“低俗”的迷恋,用扭捏作态的意图为起点,用一系列包装手法对其美化升华,从而连带**了影片在电影美学和表现技巧上的扭曲偏移。它看上去是虚空蔓延的表面意境堆砌,但在内核中却缺失了坦荡真诚的真实意境。我们**说这是某种类型的中国文人精神的延续,但它究竟值得褒扬还是怀疑,更多地牵扯到对这一支中国文化脉络的认知和判定问题。
广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