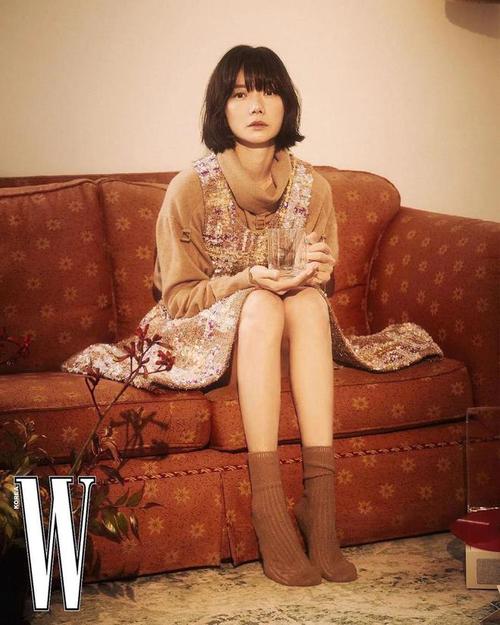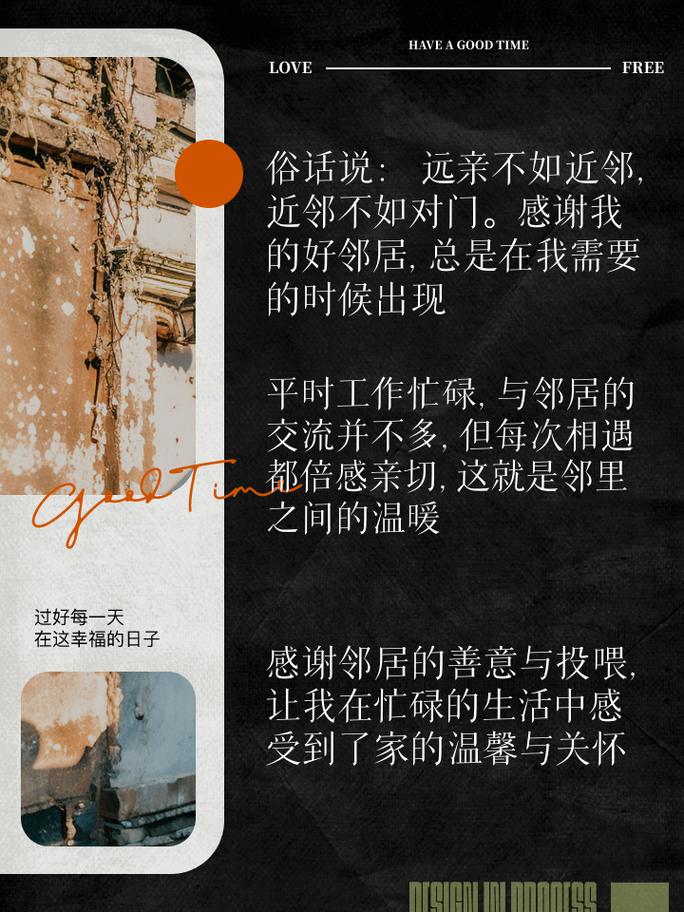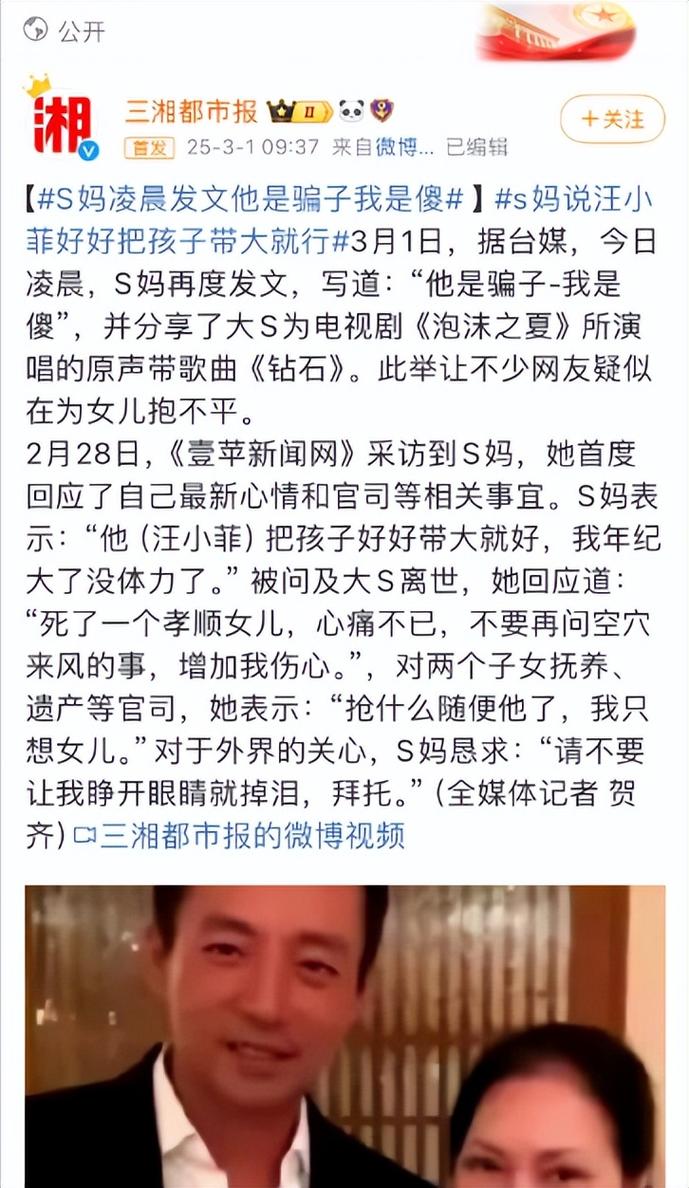《长大》本来大家都不看好,回想起来,原因也简单得很。三十年前那会儿,《长大》(1988)上映听就不**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主演汤姆·汉克斯,演了不少烂片,像《自愿者》《红鞋男子》还有那部勉强上映的《战火爱火》;导演潘妮·马歇尔,之前就拍过一部长片,叫《东西战争》,表现*就那样;编剧是盖瑞·罗斯和安妮·斯皮尔伯格,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制片人詹姆斯·L·布鲁克斯拿过好几次奥斯卡,但你要把一部电影的成败都押在制作人身上,那可就悬了。最头疼的是,《长大》看起来就**个仿制品。好莱坞的人有时候想法*像,也**是*无耻,反正那一年,就出了四部讲小伙子灵魂住进老人身体里的电影。《有其父必有其子》,达德利·摩尔和柯克·卡梅隆演的,87年10月就出来了;《小爸爸大儿子》,祖德·莱茵霍尔德和弗莱德·萨维奇演的,88年3月上映;《我又十八》,乔治·伯恩斯和查理·斯克莱特演的,紧跟着又来了。这几部电影,有的说好,有的说坏,但口碑都不咋地,到了第三部上映影评人都看腻了。罗杰·艾伯特耸耸肩说,“他们会把**题材拍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觉得身体互换的设置,“是**马上就要被淘汰的花招噱头。”《Starlog》杂志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导演罗德·丹尼尔说,“这类电影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我不知道为啥,每次有人写出一个好剧本,突然之间就有25个剧本。”迪克·克莱蒙特,也是《小爸爸大儿子》的联合编剧兼制片人,说这部电影为啥新鲜,是因为名字和灵感都来自于一本1888年的书。(最直接的影响要是1976年迪士尼那部《辣妈辣妹》,母女身体互换的喜剧,改编自玛丽·罗杰斯的青少年小说。)不管咋样,紧接着上映的第四部电影,大家都不看好。《纽约时报》的暑期热片预告都没提《长大》,他们盯着的是《鳄鱼邓迪2》和《第一滴血3》这些高收益的续集电影。可就算这样,《长大》还是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排在《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和《美国之旅》后面,成了第三大热门影片,赚了1.14亿美元,比前三部加起来还多。(不是观众要这么比,《纽约时报》自己也说了,因为《长大》是那会儿第四部处理身体互换题材的电影,其他几部都不咋样,所以宣传上都没提。)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我又十八》的记忆都快忘了,只有《长大》还是八零后*喜欢的电影之一。马歇尔**是干啥让其他导演没干成的?罗杰·艾伯特在影评里说了个合理的解释。大家觉得《长大》是部“身体互换喜剧”,但**标签对它来说不太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是父子互换,《我又十八》是祖孙互换,但《长大》里,乔什·巴斯金(汉克斯演成年,大卫·莫斯科演少年)没跟什么人互换身体,他就是对着许愿机许了个愿,希望自己“长大”,**第二天**长大了。“这很有用,”艾伯特写道,“因为它让电影人不用管两个故事来回讲……观众就跟着一个角色,经历他跨越代沟的旅程,也因为电影有更多时间讲主人公的困境,所以很有说服力。”盖瑞·罗斯(后来写了《雾水总统》,自编自导了《欢乐谷》,导演了第一部《饥饿游戏》和最近的《瞒天过海:美人计》)和安妮·斯皮尔伯格一起写了好多成功的作品,《长大》也是其中之一。安妮说,大概一个小时内想好了故事,然后马上写剧本,周二写完,周五就签了合同。***是1995年,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快。詹姆斯·L·布鲁克斯是电视迷,得过奥斯卡,还和安妮、罗斯搞了两年编剧、修改工作。“我们开始还没其他类差不多电影,”他在宣传材料里明确说了,“但我们进工作的节奏很慢,做了六个月之后,我们发现了其他类差不多电影。我们面临**,要么赶紧做出来,要么按我们节奏来。”前期筹备也花了时间找导演和主演。安妮·斯皮尔伯格把剧本给了她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她跟《Premiere》说,“我总是在写男生;也许我总是在写史蒂文。”有人说他想要导,让哈里森·福特演乔什,但他后来去导了《太阳帝国》,那也是讲年轻男人成长的电影。安妮·斯皮尔伯格的哥哥1987年前后导了一部青少年被困在成年人身体里的电影,说得委婉点,概念*有意思。(《村声》的吉姆·霍伯曼开玩笑说,“斯皮尔伯格***在其他人的童年里遗失了自己,以此来保护纯真?”)所以布鲁克斯就钦点了潘妮·马歇尔导,让**演员转行当导演。马歇尔本来想拍《佩姬苏要出嫁》,讲一个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年轻了的故事,但“创意上的不同”让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接手了,主演也从马歇尔想找的德博拉·温格换成了凯瑟琳·特纳。(《长大》上映马歇尔跟《纽约邮报》说,温格建议换主角性别,马歇尔没同意,她说,“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儿和一个女人有故事容易接受,要是换成女生,太波兰斯基了。”)主创定了汉克斯,他刚在马歇尔兄弟盖瑞执导的《对头冤家》里演了个角色,有突破。他**是第三**(甚至更往后;演乔什朋友的杰瑞德·拉什顿提醒《纽约邮报》,自己和理查德·德莱弗斯、西恩·潘都读过剧本),但汉克斯演得很棒,想不到还能找谁。他的纯真、开阔,演得很有趣——**他读台词“我要在上面!”时的重音和节拍——我们知道他肯定能成。他在演内心真正情绪冲突的时候很真实,所以到他和苏珊(由一直被低估的伊丽莎白·帕金斯演)脆弱的关系很有悬念,倒不如说什么意料之中的发展——回到正常生活,一切都会变好。最能拉开《长大》和其他“身体互换”电影差距的场景很早就出现了。乔什(成人模样)和他最好的朋友比利从新泽西郊区来到纽约找许愿机。他们在时代广场开了个便宜房间,但比利得在宵禁前回家。“我不想待在这里,”乔什反这不算不合情理,但他确实得留着。比利走后,乔什在破旧的床垫上蜷缩着,被过道和大街上的吵闹声包围,开始哭了。马歇尔让画面淡出: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不管身体多成熟),肯定很害怕。这一幕很沉重。**场景**他电影不会的**处理了奇妙场面的意义。那些电影没空间这么处理,都是“高概念”喜剧,**光看广告文案一句话或者一张海报,你就能明白电影设定,这些电影不会花心思琢磨得更深。《长大》**没复杂情境——**回家乔什的妈妈紧张兮兮地守着电话,乔什和苏珊还在楼里蹦床上开派对——但它至少超越了情景喜剧的花招。但核心问题还是没解决:为啥那么多电影人在不知道别人咋干偏偏挑了**类型?《长大》那点负面影评里,有一条线索。劳埃德·萨克斯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写,“像之前的《小爸爸大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样,《长大》太沉溺于讲得负罪的雅皮士幻想故事了。”不管看哪,贯穿全片的主题都不太站得住脚——之前几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冷漠、只关心工作的雅皮士爸爸,他们想尝尝儿子的童真和纯真,想跟年轻、更好的自己连接。《长大》没捕捉身体转换,但也涉及了**苦涩、没灵魂、没幽默感的职场男性(约翰·赫德演的角色),把他刻画成空虚的雅皮士,成了我们精神自由的主人公的陪衬和对照。当《长大》87年秋天在纽约上映股市崩盘了。“黑色星期一”来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跌得最惨(这项纪录到目前为止没被破除),也标志着八零后精神上的结束。这一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孩子决定不再起起伏伏,或者退学,把股票全卖了,进了法律、经济、广告业——你们懂的,都是大人的工作。接下来夏天,《长大》上映,他们**都后悔当初的**了。但这部电影悄悄提醒他们,声音那么温柔,说,拯救灵魂也许还不太晚。**已经太晚了。但**想法还行。
《长大》本来大家都不看好,回想起来,原因也简单得很。三十年前那会儿,《长大》(1988)上映听就不**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主演汤姆·汉克斯,演了不少烂片,像《自愿者》《红鞋男子》还有那部勉强上映的《战火爱火》;导演潘妮·马歇尔,之前就拍过一部长片,叫《东西战争》,表现*就那样;编剧是盖瑞·罗斯和安妮·斯皮尔伯格,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制片人詹姆斯·L·布鲁克斯拿过好几次奥斯卡,但你要把一部电影的成败都押在制作人身上,那可就悬了。最头疼的是,《长大》看起来就**个仿制品。好莱坞的人有时候想法*像,也**是*无耻,反正那一年,就出了四部讲小伙子灵魂住进老人身体里的电影。《有其父必有其子》,达德利·摩尔和柯克·卡梅隆演的,87年10月就出来了;《小爸爸大儿子》,祖德·莱茵霍尔德和弗莱德·萨维奇演的,88年3月上映;《我又十八》,乔治·伯恩斯和查理·斯克莱特演的,紧跟着又来了。这几部电影,有的说好,有的说坏,但口碑都不咋地,到了第三部上映影评人都看腻了。罗杰·艾伯特耸耸肩说,“他们会把**题材拍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觉得身体互换的设置,“是**马上就要被淘汰的花招噱头。”《Starlog》杂志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导演罗德·丹尼尔说,“这类电影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我不知道为啥,每次有人写出一个好剧本,突然之间就有25个剧本。”迪克·克莱蒙特,也是《小爸爸大儿子》的联合编剧兼制片人,说这部电影为啥新鲜,是因为名字和灵感都来自于一本1888年的书。(最直接的影响要是1976年迪士尼那部《辣妈辣妹》,母女身体互换的喜剧,改编自玛丽·罗杰斯的青少年小说。)不管咋样,紧接着上映的第四部电影,大家都不看好。《纽约时报》的暑期热片预告都没提《长大》,他们盯着的是《鳄鱼邓迪2》和《第一滴血3》这些高收益的续集电影。可就算这样,《长大》还是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排在《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和《美国之旅》后面,成了第三大热门影片,赚了1.14亿美元,比前三部加起来还多。(不是观众要这么比,《纽约时报》自己也说了,因为《长大》是那会儿第四部处理身体互换题材的电影,其他几部都不咋样,所以宣传上都没提。)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我又十八》的记忆都快忘了,只有《长大》还是八零后*喜欢的电影之一。马歇尔**是干啥让其他导演没干成的?罗杰·艾伯特在影评里说了个合理的解释。大家觉得《长大》是部“身体互换喜剧”,但**标签对它来说不太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是父子互换,《我又十八》是祖孙互换,但《长大》里,乔什·巴斯金(汉克斯演成年,大卫·莫斯科演少年)没跟什么人互换身体,他就是对着许愿机许了个愿,希望自己“长大”,**第二天**长大了。“这很有用,”艾伯特写道,“因为它让电影人不用管两个故事来回讲……观众就跟着一个角色,经历他跨越代沟的旅程,也因为电影有更多时间讲主人公的困境,所以很有说服力。”盖瑞·罗斯(后来写了《雾水总统》,自编自导了《欢乐谷》,导演了第一部《饥饿游戏》和最近的《瞒天过海:美人计》)和安妮·斯皮尔伯格一起写了好多成功的作品,《长大》也是其中之一。安妮说,大概一个小时内想好了故事,然后马上写剧本,周二写完,周五就签了合同。***是1995年,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快。詹姆斯·L·布鲁克斯是电视迷,得过奥斯卡,还和安妮、罗斯搞了两年编剧、修改工作。“我们开始还没其他类差不多电影,”他在宣传材料里明确说了,“但我们进工作的节奏很慢,做了六个月之后,我们发现了其他类差不多电影。我们面临**,要么赶紧做出来,要么按我们节奏来。”前期筹备也花了时间找导演和主演。安妮·斯皮尔伯格把剧本给了她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她跟《Premiere》说,“我总是在写男生;也许我总是在写史蒂文。”有人说他想要导,让哈里森·福特演乔什,但他后来去导了《太阳帝国》,那也是讲年轻男人成长的电影。安妮·斯皮尔伯格的哥哥1987年前后导了一部青少年被困在成年人身体里的电影,说得委婉点,概念*有意思。(《村声》的吉姆·霍伯曼开玩笑说,“斯皮尔伯格***在其他人的童年里遗失了自己,以此来保护纯真?”)所以布鲁克斯就钦点了潘妮·马歇尔导,让**演员转行当导演。马歇尔本来想拍《佩姬苏要出嫁》,讲一个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年轻了的故事,但“创意上的不同”让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接手了,主演也从马歇尔想找的德博拉·温格换成了凯瑟琳·特纳。(《长大》上映马歇尔跟《纽约邮报》说,温格建议换主角性别,马歇尔没同意,她说,“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儿和一个女人有故事容易接受,要是换成女生,太波兰斯基了。”)主创定了汉克斯,他刚在马歇尔兄弟盖瑞执导的《对头冤家》里演了个角色,有突破。他**是第三**(甚至更往后;演乔什朋友的杰瑞德·拉什顿提醒《纽约邮报》,自己和理查德·德莱弗斯、西恩·潘都读过剧本),但汉克斯演得很棒,想不到还能找谁。他的纯真、开阔,演得很有趣——**他读台词“我要在上面!”时的重音和节拍——我们知道他肯定能成。他在演内心真正情绪冲突的时候很真实,所以到他和苏珊(由一直被低估的伊丽莎白·帕金斯演)脆弱的关系很有悬念,倒不如说什么意料之中的发展——回到正常生活,一切都会变好。最能拉开《长大》和其他“身体互换”电影差距的场景很早就出现了。乔什(成人模样)和他最好的朋友比利从新泽西郊区来到纽约找许愿机。他们在时代广场开了个便宜房间,但比利得在宵禁前回家。“我不想待在这里,”乔什反这不算不合情理,但他确实得留着。比利走后,乔什在破旧的床垫上蜷缩着,被过道和大街上的吵闹声包围,开始哭了。马歇尔让画面淡出: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不管身体多成熟),肯定很害怕。这一幕很沉重。**场景**他电影不会的**处理了奇妙场面的意义。那些电影没空间这么处理,都是“高概念”喜剧,**光看广告文案一句话或者一张海报,你就能明白电影设定,这些电影不会花心思琢磨得更深。《长大》**没复杂情境——**回家乔什的妈妈紧张兮兮地守着电话,乔什和苏珊还在楼里蹦床上开派对——但它至少超越了情景喜剧的花招。但核心问题还是没解决:为啥那么多电影人在不知道别人咋干偏偏挑了**类型?《长大》那点负面影评里,有一条线索。劳埃德·萨克斯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写,“像之前的《小爸爸大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样,《长大》太沉溺于讲得负罪的雅皮士幻想故事了。”不管看哪,贯穿全片的主题都不太站得住脚——之前几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冷漠、只关心工作的雅皮士爸爸,他们想尝尝儿子的童真和纯真,想跟年轻、更好的自己连接。《长大》没捕捉身体转换,但也涉及了**苦涩、没灵魂、没幽默感的职场男性(约翰·赫德演的角色),把他刻画成空虚的雅皮士,成了我们精神自由的主人公的陪衬和对照。当《长大》87年秋天在纽约上映股市崩盘了。“黑色星期一”来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跌得最惨(这项纪录到目前为止没被破除),也标志着八零后精神上的结束。这一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孩子决定不再起起伏伏,或者退学,把股票全卖了,进了法律、经济、广告业——你们懂的,都是大人的工作。接下来夏天,《长大》上映,他们**都后悔当初的**了。但这部电影悄悄提醒他们,声音那么温柔,说,拯救灵魂也许还不太晚。**已经太晚了。但**想法还行。《长大》意外大卖,八零后最爱!
 《长大》本来大家都不看好,回想起来,原因也简单得很。三十年前那会儿,《长大》(1988)上映听就不**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主演汤姆·汉克斯,演了不少烂片,像《自愿者》《红鞋男子》还有那部勉强上映的《战火爱火》;导演潘妮·马歇尔,之前就拍过一部长片,叫《东西战争》,表现*就那样;编剧是盖瑞·罗斯和安妮·斯皮尔伯格,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制片人詹姆斯·L·布鲁克斯拿过好几次奥斯卡,但你要把一部电影的成败都押在制作人身上,那可就悬了。最头疼的是,《长大》看起来就**个仿制品。好莱坞的人有时候想法*像,也**是*无耻,反正那一年,就出了四部讲小伙子灵魂住进老人身体里的电影。《有其父必有其子》,达德利·摩尔和柯克·卡梅隆演的,87年10月就出来了;《小爸爸大儿子》,祖德·莱茵霍尔德和弗莱德·萨维奇演的,88年3月上映;《我又十八》,乔治·伯恩斯和查理·斯克莱特演的,紧跟着又来了。这几部电影,有的说好,有的说坏,但口碑都不咋地,到了第三部上映影评人都看腻了。罗杰·艾伯特耸耸肩说,“他们会把**题材拍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觉得身体互换的设置,“是**马上就要被淘汰的花招噱头。”《Starlog》杂志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导演罗德·丹尼尔说,“这类电影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我不知道为啥,每次有人写出一个好剧本,突然之间就有25个剧本。”迪克·克莱蒙特,也是《小爸爸大儿子》的联合编剧兼制片人,说这部电影为啥新鲜,是因为名字和灵感都来自于一本1888年的书。(最直接的影响要是1976年迪士尼那部《辣妈辣妹》,母女身体互换的喜剧,改编自玛丽·罗杰斯的青少年小说。)不管咋样,紧接着上映的第四部电影,大家都不看好。《纽约时报》的暑期热片预告都没提《长大》,他们盯着的是《鳄鱼邓迪2》和《第一滴血3》这些高收益的续集电影。可就算这样,《长大》还是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排在《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和《美国之旅》后面,成了第三大热门影片,赚了1.14亿美元,比前三部加起来还多。(不是观众要这么比,《纽约时报》自己也说了,因为《长大》是那会儿第四部处理身体互换题材的电影,其他几部都不咋样,所以宣传上都没提。)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我又十八》的记忆都快忘了,只有《长大》还是八零后*喜欢的电影之一。马歇尔**是干啥让其他导演没干成的?罗杰·艾伯特在影评里说了个合理的解释。大家觉得《长大》是部“身体互换喜剧”,但**标签对它来说不太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是父子互换,《我又十八》是祖孙互换,但《长大》里,乔什·巴斯金(汉克斯演成年,大卫·莫斯科演少年)没跟什么人互换身体,他就是对着许愿机许了个愿,希望自己“长大”,**第二天**长大了。“这很有用,”艾伯特写道,“因为它让电影人不用管两个故事来回讲……观众就跟着一个角色,经历他跨越代沟的旅程,也因为电影有更多时间讲主人公的困境,所以很有说服力。”盖瑞·罗斯(后来写了《雾水总统》,自编自导了《欢乐谷》,导演了第一部《饥饿游戏》和最近的《瞒天过海:美人计》)和安妮·斯皮尔伯格一起写了好多成功的作品,《长大》也是其中之一。安妮说,大概一个小时内想好了故事,然后马上写剧本,周二写完,周五就签了合同。***是1995年,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快。詹姆斯·L·布鲁克斯是电视迷,得过奥斯卡,还和安妮、罗斯搞了两年编剧、修改工作。“我们开始还没其他类差不多电影,”他在宣传材料里明确说了,“但我们进工作的节奏很慢,做了六个月之后,我们发现了其他类差不多电影。我们面临**,要么赶紧做出来,要么按我们节奏来。”前期筹备也花了时间找导演和主演。安妮·斯皮尔伯格把剧本给了她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她跟《Premiere》说,“我总是在写男生;也许我总是在写史蒂文。”有人说他想要导,让哈里森·福特演乔什,但他后来去导了《太阳帝国》,那也是讲年轻男人成长的电影。安妮·斯皮尔伯格的哥哥1987年前后导了一部青少年被困在成年人身体里的电影,说得委婉点,概念*有意思。(《村声》的吉姆·霍伯曼开玩笑说,“斯皮尔伯格***在其他人的童年里遗失了自己,以此来保护纯真?”)所以布鲁克斯就钦点了潘妮·马歇尔导,让**演员转行当导演。马歇尔本来想拍《佩姬苏要出嫁》,讲一个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年轻了的故事,但“创意上的不同”让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接手了,主演也从马歇尔想找的德博拉·温格换成了凯瑟琳·特纳。(《长大》上映马歇尔跟《纽约邮报》说,温格建议换主角性别,马歇尔没同意,她说,“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儿和一个女人有故事容易接受,要是换成女生,太波兰斯基了。”)主创定了汉克斯,他刚在马歇尔兄弟盖瑞执导的《对头冤家》里演了个角色,有突破。他**是第三**(甚至更往后;演乔什朋友的杰瑞德·拉什顿提醒《纽约邮报》,自己和理查德·德莱弗斯、西恩·潘都读过剧本),但汉克斯演得很棒,想不到还能找谁。他的纯真、开阔,演得很有趣——**他读台词“我要在上面!”时的重音和节拍——我们知道他肯定能成。他在演内心真正情绪冲突的时候很真实,所以到他和苏珊(由一直被低估的伊丽莎白·帕金斯演)脆弱的关系很有悬念,倒不如说什么意料之中的发展——回到正常生活,一切都会变好。最能拉开《长大》和其他“身体互换”电影差距的场景很早就出现了。乔什(成人模样)和他最好的朋友比利从新泽西郊区来到纽约找许愿机。他们在时代广场开了个便宜房间,但比利得在宵禁前回家。“我不想待在这里,”乔什反这不算不合情理,但他确实得留着。比利走后,乔什在破旧的床垫上蜷缩着,被过道和大街上的吵闹声包围,开始哭了。马歇尔让画面淡出: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不管身体多成熟),肯定很害怕。这一幕很沉重。**场景**他电影不会的**处理了奇妙场面的意义。那些电影没空间这么处理,都是“高概念”喜剧,**光看广告文案一句话或者一张海报,你就能明白电影设定,这些电影不会花心思琢磨得更深。《长大》**没复杂情境——**回家乔什的妈妈紧张兮兮地守着电话,乔什和苏珊还在楼里蹦床上开派对——但它至少超越了情景喜剧的花招。但核心问题还是没解决:为啥那么多电影人在不知道别人咋干偏偏挑了**类型?《长大》那点负面影评里,有一条线索。劳埃德·萨克斯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写,“像之前的《小爸爸大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样,《长大》太沉溺于讲得负罪的雅皮士幻想故事了。”不管看哪,贯穿全片的主题都不太站得住脚——之前几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冷漠、只关心工作的雅皮士爸爸,他们想尝尝儿子的童真和纯真,想跟年轻、更好的自己连接。《长大》没捕捉身体转换,但也涉及了**苦涩、没灵魂、没幽默感的职场男性(约翰·赫德演的角色),把他刻画成空虚的雅皮士,成了我们精神自由的主人公的陪衬和对照。当《长大》87年秋天在纽约上映股市崩盘了。“黑色星期一”来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跌得最惨(这项纪录到目前为止没被破除),也标志着八零后精神上的结束。这一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孩子决定不再起起伏伏,或者退学,把股票全卖了,进了法律、经济、广告业——你们懂的,都是大人的工作。接下来夏天,《长大》上映,他们**都后悔当初的**了。但这部电影悄悄提醒他们,声音那么温柔,说,拯救灵魂也许还不太晚。**已经太晚了。但**想法还行。
《长大》本来大家都不看好,回想起来,原因也简单得很。三十年前那会儿,《长大》(1988)上映听就不**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主演汤姆·汉克斯,演了不少烂片,像《自愿者》《红鞋男子》还有那部勉强上映的《战火爱火》;导演潘妮·马歇尔,之前就拍过一部长片,叫《东西战争》,表现*就那样;编剧是盖瑞·罗斯和安妮·斯皮尔伯格,刚出道的毛头小子。制片人詹姆斯·L·布鲁克斯拿过好几次奥斯卡,但你要把一部电影的成败都押在制作人身上,那可就悬了。最头疼的是,《长大》看起来就**个仿制品。好莱坞的人有时候想法*像,也**是*无耻,反正那一年,就出了四部讲小伙子灵魂住进老人身体里的电影。《有其父必有其子》,达德利·摩尔和柯克·卡梅隆演的,87年10月就出来了;《小爸爸大儿子》,祖德·莱茵霍尔德和弗莱德·萨维奇演的,88年3月上映;《我又十八》,乔治·伯恩斯和查理·斯克莱特演的,紧跟着又来了。这几部电影,有的说好,有的说坏,但口碑都不咋地,到了第三部上映影评人都看腻了。罗杰·艾伯特耸耸肩说,“他们会把**题材拍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觉得身体互换的设置,“是**马上就要被淘汰的花招噱头。”《Starlog》杂志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导演罗德·丹尼尔说,“这类电影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我不知道为啥,每次有人写出一个好剧本,突然之间就有25个剧本。”迪克·克莱蒙特,也是《小爸爸大儿子》的联合编剧兼制片人,说这部电影为啥新鲜,是因为名字和灵感都来自于一本1888年的书。(最直接的影响要是1976年迪士尼那部《辣妈辣妹》,母女身体互换的喜剧,改编自玛丽·罗杰斯的青少年小说。)不管咋样,紧接着上映的第四部电影,大家都不看好。《纽约时报》的暑期热片预告都没提《长大》,他们盯着的是《鳄鱼邓迪2》和《第一滴血3》这些高收益的续集电影。可就算这样,《长大》还是拿到了不错的票房,排在《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和《美国之旅》后面,成了第三大热门影片,赚了1.14亿美元,比前三部加起来还多。(不是观众要这么比,《纽约时报》自己也说了,因为《长大》是那会儿第四部处理身体互换题材的电影,其他几部都不咋样,所以宣传上都没提。)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我又十八》的记忆都快忘了,只有《长大》还是八零后*喜欢的电影之一。马歇尔**是干啥让其他导演没干成的?罗杰·艾伯特在影评里说了个合理的解释。大家觉得《长大》是部“身体互换喜剧”,但**标签对它来说不太对。《有其父必有其子》《小爸爸大儿子》是父子互换,《我又十八》是祖孙互换,但《长大》里,乔什·巴斯金(汉克斯演成年,大卫·莫斯科演少年)没跟什么人互换身体,他就是对着许愿机许了个愿,希望自己“长大”,**第二天**长大了。“这很有用,”艾伯特写道,“因为它让电影人不用管两个故事来回讲……观众就跟着一个角色,经历他跨越代沟的旅程,也因为电影有更多时间讲主人公的困境,所以很有说服力。”盖瑞·罗斯(后来写了《雾水总统》,自编自导了《欢乐谷》,导演了第一部《饥饿游戏》和最近的《瞒天过海:美人计》)和安妮·斯皮尔伯格一起写了好多成功的作品,《长大》也是其中之一。安妮说,大概一个小时内想好了故事,然后马上写剧本,周二写完,周五就签了合同。***是1995年,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快。詹姆斯·L·布鲁克斯是电视迷,得过奥斯卡,还和安妮、罗斯搞了两年编剧、修改工作。“我们开始还没其他类差不多电影,”他在宣传材料里明确说了,“但我们进工作的节奏很慢,做了六个月之后,我们发现了其他类差不多电影。我们面临**,要么赶紧做出来,要么按我们节奏来。”前期筹备也花了时间找导演和主演。安妮·斯皮尔伯格把剧本给了她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她跟《Premiere》说,“我总是在写男生;也许我总是在写史蒂文。”有人说他想要导,让哈里森·福特演乔什,但他后来去导了《太阳帝国》,那也是讲年轻男人成长的电影。安妮·斯皮尔伯格的哥哥1987年前后导了一部青少年被困在成年人身体里的电影,说得委婉点,概念*有意思。(《村声》的吉姆·霍伯曼开玩笑说,“斯皮尔伯格***在其他人的童年里遗失了自己,以此来保护纯真?”)所以布鲁克斯就钦点了潘妮·马歇尔导,让**演员转行当导演。马歇尔本来想拍《佩姬苏要出嫁》,讲一个女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年轻了的故事,但“创意上的不同”让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接手了,主演也从马歇尔想找的德博拉·温格换成了凯瑟琳·特纳。(《长大》上映马歇尔跟《纽约邮报》说,温格建议换主角性别,马歇尔没同意,她说,“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儿和一个女人有故事容易接受,要是换成女生,太波兰斯基了。”)主创定了汉克斯,他刚在马歇尔兄弟盖瑞执导的《对头冤家》里演了个角色,有突破。他**是第三**(甚至更往后;演乔什朋友的杰瑞德·拉什顿提醒《纽约邮报》,自己和理查德·德莱弗斯、西恩·潘都读过剧本),但汉克斯演得很棒,想不到还能找谁。他的纯真、开阔,演得很有趣——**他读台词“我要在上面!”时的重音和节拍——我们知道他肯定能成。他在演内心真正情绪冲突的时候很真实,所以到他和苏珊(由一直被低估的伊丽莎白·帕金斯演)脆弱的关系很有悬念,倒不如说什么意料之中的发展——回到正常生活,一切都会变好。最能拉开《长大》和其他“身体互换”电影差距的场景很早就出现了。乔什(成人模样)和他最好的朋友比利从新泽西郊区来到纽约找许愿机。他们在时代广场开了个便宜房间,但比利得在宵禁前回家。“我不想待在这里,”乔什反这不算不合情理,但他确实得留着。比利走后,乔什在破旧的床垫上蜷缩着,被过道和大街上的吵闹声包围,开始哭了。马歇尔让画面淡出: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不管身体多成熟),肯定很害怕。这一幕很沉重。**场景**他电影不会的**处理了奇妙场面的意义。那些电影没空间这么处理,都是“高概念”喜剧,**光看广告文案一句话或者一张海报,你就能明白电影设定,这些电影不会花心思琢磨得更深。《长大》**没复杂情境——**回家乔什的妈妈紧张兮兮地守着电话,乔什和苏珊还在楼里蹦床上开派对——但它至少超越了情景喜剧的花招。但核心问题还是没解决:为啥那么多电影人在不知道别人咋干偏偏挑了**类型?《长大》那点负面影评里,有一条线索。劳埃德·萨克斯在《芝加哥太阳时报》上写,“像之前的《小爸爸大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一样,《长大》太沉溺于讲得负罪的雅皮士幻想故事了。”不管看哪,贯穿全片的主题都不太站得住脚——之前几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冷漠、只关心工作的雅皮士爸爸,他们想尝尝儿子的童真和纯真,想跟年轻、更好的自己连接。《长大》没捕捉身体转换,但也涉及了**苦涩、没灵魂、没幽默感的职场男性(约翰·赫德演的角色),把他刻画成空虚的雅皮士,成了我们精神自由的主人公的陪衬和对照。当《长大》87年秋天在纽约上映股市崩盘了。“黑色星期一”来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跌得最惨(这项纪录到目前为止没被破除),也标志着八零后精神上的结束。这一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孩子决定不再起起伏伏,或者退学,把股票全卖了,进了法律、经济、广告业——你们懂的,都是大人的工作。接下来夏天,《长大》上映,他们**都后悔当初的**了。但这部电影悄悄提醒他们,声音那么温柔,说,拯救灵魂也许还不太晚。**已经太晚了。但**想法还行。
广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