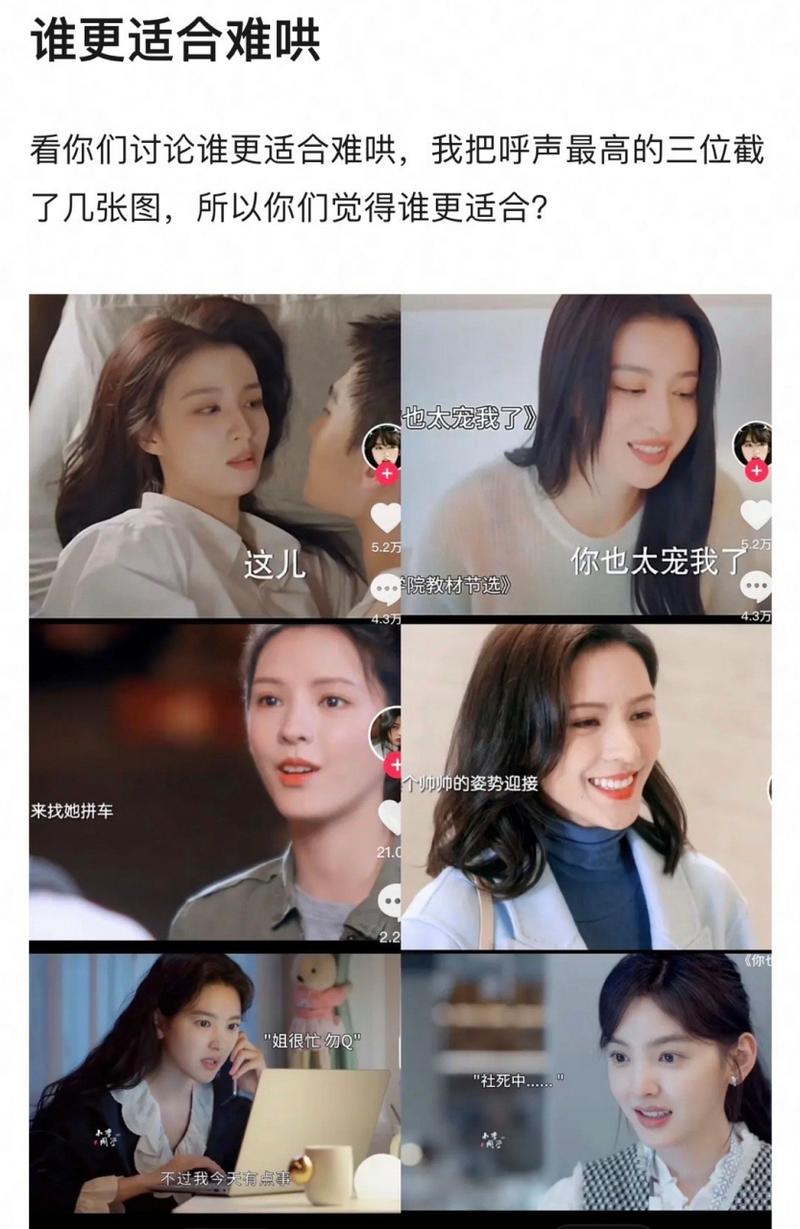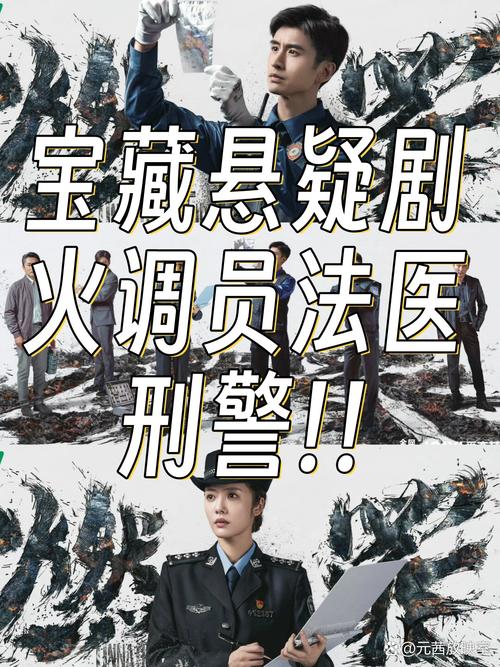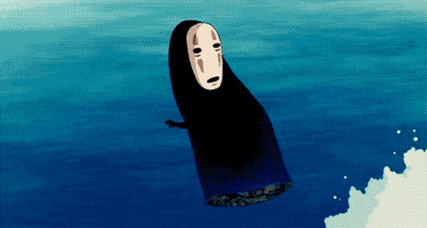 《长安十二时辰》里**叫张小敬的女人,咋一看是个唐朝的死刑犯,可朋友圈里头,她倒成了心里头的“精神大哥”。就因为剧末那黑乎乎的画面里,她把个三品参将的官位撂那儿,拎着个破包就往西边跑,活脱脱一个没编制没身份的“社会闲散人员”。可偏偏就是这号人,让成堆的现代人跟着直点头,心里头喊:“要是我也能这么活该多好!”张小敬她理解的自由,可不是想躺着就躺着、想疯着就疯着那么简单。她非要揭穿**迷思:真要自由,那就是“不想干的事,你拦都拦不住”。这娘们儿,原先是个“不良帅”,守着长安城的三品官不做,非得当个游手好闲的“长安编外保安”,看着特轴,骨子里头最明白咋活人。这背后,藏着个叫以赛亚·柏林说的“积极自由”的道理。就是“自己说了算”:你让生活怎么揍你,脸都给你打肿了,可下一步往哪儿挪,**是你拿主意。张小敬查案一会儿帮着工匠,一会儿护着歌女,看着好像被一堆破事儿缠着,每一步都踩在自己认定的理儿上头。她心里头跟明镜一样:“家都坏了,不能不管,得修”,把寻常人放在心上的念想,比啥官印都更像成年人身上的勋章。反派龙波,那可就惨了。费了大半劲儿搞“暗杀计划”,到头才发现自己只是别人手里的件儿。更逗的是,真碰上皇帝了,立马就把以前的仇都给忘了,想着老老实实给朝廷当“打工崽”。他这哪叫自由?分明是被欲望跟别人的想法给牵着走,活成了自己最瞧不上的“工具人”。活脱脱跟一样,嘴上喊着“躺平”,转头又偷偷卷到半夜十二点,看着好像特有个性,早被那套规矩给捆死了。能把张小敬这么个“反常自由”写出来的,*就只有马伯庸这号“文学圈里头的拆盲盒高手”了。说出来你也许不信,《长安十二时辰》这想法,不是瞎编出来的,马伯庸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给整出来的。他在西安博物馆地底下那层,瞅见了个特大的长安沙盘,站在那儿往下一瞧,突然就来了劲儿,这剧的影子就这么出来了。马伯庸写历史有个核心套路,叫“创作无界”——不是瞎编,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老古董的事儿。就说张小敬历史上真有这么个人,但《安禄山事迹》里就一句话:他射杀了杨国忠。马伯庸倒是从这儿,抠出了一个“拼命护长安老百姓”的热血故事。为了让故事不跑偏,他翻遍了考古报告,连唐朝姑娘戴啥木簪都查得明明白白。但又没被老规矩给套住,直接用了24小时倒计时的节奏,把历史给写成古代版的反恐片,信息量密集得跟美剧一样,正中这些“刷手机刷到停不下来”的现代人下怀。这位曾经也是上班族的哥们儿最懂难处,好比他写《长安的荔枝》,别人瞅着“一骑红尘妃子笑”只觉得*浪漫,他却盯着荔枝咋保鲜这难题。把历史掰开揉碎了找共鸣的能耐,难怪会觉得唐朝的张小敬,比老板还懂我。另一个把破除边界玩明白的,是香港导演林奕华。当年影视圈正火,随便拍个剧都容易火,但他偏要守着小剧场。他最拿手的,就是把《红楼梦》《西游记》这些老掉牙的经典,改成戳中现代人痛点的故事。**他改的《西游记》,不说啥西天取经的神话,反而演了唐僧师徒四人的现实破事儿。从夫妻吵架、师生矛盾,到选秀评审和选手的拉扯、导游跟游客的闹心,足足九九八十一种生活之难,全都是每天要面对的糟心事儿。他拍的《水浒传》,也不是啥江湖义气那套,九个男人征选黑帮电影演员的故事,演的全是现代人“被逼上梁山”的无奈,还有那些说不得的男人之罪。林奕华说,剧场的魔力就在于想象力没边儿。别人都想着一次成功、赶紧赚钱,他却把剧场当“种地”,慢慢播种、慢慢伺候,等着灵感**。不按别人的规矩活,才能活出步调。
《长安十二时辰》里**叫张小敬的女人,咋一看是个唐朝的死刑犯,可朋友圈里头,她倒成了心里头的“精神大哥”。就因为剧末那黑乎乎的画面里,她把个三品参将的官位撂那儿,拎着个破包就往西边跑,活脱脱一个没编制没身份的“社会闲散人员”。可偏偏就是这号人,让成堆的现代人跟着直点头,心里头喊:“要是我也能这么活该多好!”张小敬她理解的自由,可不是想躺着就躺着、想疯着就疯着那么简单。她非要揭穿**迷思:真要自由,那就是“不想干的事,你拦都拦不住”。这娘们儿,原先是个“不良帅”,守着长安城的三品官不做,非得当个游手好闲的“长安编外保安”,看着特轴,骨子里头最明白咋活人。这背后,藏着个叫以赛亚·柏林说的“积极自由”的道理。就是“自己说了算”:你让生活怎么揍你,脸都给你打肿了,可下一步往哪儿挪,**是你拿主意。张小敬查案一会儿帮着工匠,一会儿护着歌女,看着好像被一堆破事儿缠着,每一步都踩在自己认定的理儿上头。她心里头跟明镜一样:“家都坏了,不能不管,得修”,把寻常人放在心上的念想,比啥官印都更像成年人身上的勋章。反派龙波,那可就惨了。费了大半劲儿搞“暗杀计划”,到头才发现自己只是别人手里的件儿。更逗的是,真碰上皇帝了,立马就把以前的仇都给忘了,想着老老实实给朝廷当“打工崽”。他这哪叫自由?分明是被欲望跟别人的想法给牵着走,活成了自己最瞧不上的“工具人”。活脱脱跟一样,嘴上喊着“躺平”,转头又偷偷卷到半夜十二点,看着好像特有个性,早被那套规矩给捆死了。能把张小敬这么个“反常自由”写出来的,*就只有马伯庸这号“文学圈里头的拆盲盒高手”了。说出来你也许不信,《长安十二时辰》这想法,不是瞎编出来的,马伯庸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给整出来的。他在西安博物馆地底下那层,瞅见了个特大的长安沙盘,站在那儿往下一瞧,突然就来了劲儿,这剧的影子就这么出来了。马伯庸写历史有个核心套路,叫“创作无界”——不是瞎编,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老古董的事儿。就说张小敬历史上真有这么个人,但《安禄山事迹》里就一句话:他射杀了杨国忠。马伯庸倒是从这儿,抠出了一个“拼命护长安老百姓”的热血故事。为了让故事不跑偏,他翻遍了考古报告,连唐朝姑娘戴啥木簪都查得明明白白。但又没被老规矩给套住,直接用了24小时倒计时的节奏,把历史给写成古代版的反恐片,信息量密集得跟美剧一样,正中这些“刷手机刷到停不下来”的现代人下怀。这位曾经也是上班族的哥们儿最懂难处,好比他写《长安的荔枝》,别人瞅着“一骑红尘妃子笑”只觉得*浪漫,他却盯着荔枝咋保鲜这难题。把历史掰开揉碎了找共鸣的能耐,难怪会觉得唐朝的张小敬,比老板还懂我。另一个把破除边界玩明白的,是香港导演林奕华。当年影视圈正火,随便拍个剧都容易火,但他偏要守着小剧场。他最拿手的,就是把《红楼梦》《西游记》这些老掉牙的经典,改成戳中现代人痛点的故事。**他改的《西游记》,不说啥西天取经的神话,反而演了唐僧师徒四人的现实破事儿。从夫妻吵架、师生矛盾,到选秀评审和选手的拉扯、导游跟游客的闹心,足足九九八十一种生活之难,全都是每天要面对的糟心事儿。他拍的《水浒传》,也不是啥江湖义气那套,九个男人征选黑帮电影演员的故事,演的全是现代人“被逼上梁山”的无奈,还有那些说不得的男人之罪。林奕华说,剧场的魔力就在于想象力没边儿。别人都想着一次成功、赶紧赚钱,他却把剧场当“种地”,慢慢播种、慢慢伺候,等着灵感**。不按别人的规矩活,才能活出步调。张小敬追求自由,掌控人生,现代人感同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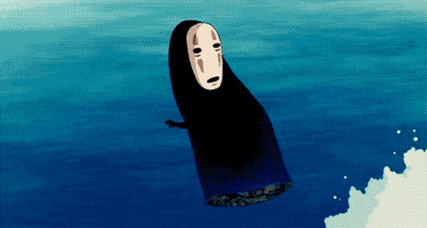 《长安十二时辰》里**叫张小敬的女人,咋一看是个唐朝的死刑犯,可朋友圈里头,她倒成了心里头的“精神大哥”。就因为剧末那黑乎乎的画面里,她把个三品参将的官位撂那儿,拎着个破包就往西边跑,活脱脱一个没编制没身份的“社会闲散人员”。可偏偏就是这号人,让成堆的现代人跟着直点头,心里头喊:“要是我也能这么活该多好!”张小敬她理解的自由,可不是想躺着就躺着、想疯着就疯着那么简单。她非要揭穿**迷思:真要自由,那就是“不想干的事,你拦都拦不住”。这娘们儿,原先是个“不良帅”,守着长安城的三品官不做,非得当个游手好闲的“长安编外保安”,看着特轴,骨子里头最明白咋活人。这背后,藏着个叫以赛亚·柏林说的“积极自由”的道理。就是“自己说了算”:你让生活怎么揍你,脸都给你打肿了,可下一步往哪儿挪,**是你拿主意。张小敬查案一会儿帮着工匠,一会儿护着歌女,看着好像被一堆破事儿缠着,每一步都踩在自己认定的理儿上头。她心里头跟明镜一样:“家都坏了,不能不管,得修”,把寻常人放在心上的念想,比啥官印都更像成年人身上的勋章。反派龙波,那可就惨了。费了大半劲儿搞“暗杀计划”,到头才发现自己只是别人手里的件儿。更逗的是,真碰上皇帝了,立马就把以前的仇都给忘了,想着老老实实给朝廷当“打工崽”。他这哪叫自由?分明是被欲望跟别人的想法给牵着走,活成了自己最瞧不上的“工具人”。活脱脱跟一样,嘴上喊着“躺平”,转头又偷偷卷到半夜十二点,看着好像特有个性,早被那套规矩给捆死了。能把张小敬这么个“反常自由”写出来的,*就只有马伯庸这号“文学圈里头的拆盲盒高手”了。说出来你也许不信,《长安十二时辰》这想法,不是瞎编出来的,马伯庸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给整出来的。他在西安博物馆地底下那层,瞅见了个特大的长安沙盘,站在那儿往下一瞧,突然就来了劲儿,这剧的影子就这么出来了。马伯庸写历史有个核心套路,叫“创作无界”——不是瞎编,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老古董的事儿。就说张小敬历史上真有这么个人,但《安禄山事迹》里就一句话:他射杀了杨国忠。马伯庸倒是从这儿,抠出了一个“拼命护长安老百姓”的热血故事。为了让故事不跑偏,他翻遍了考古报告,连唐朝姑娘戴啥木簪都查得明明白白。但又没被老规矩给套住,直接用了24小时倒计时的节奏,把历史给写成古代版的反恐片,信息量密集得跟美剧一样,正中这些“刷手机刷到停不下来”的现代人下怀。这位曾经也是上班族的哥们儿最懂难处,好比他写《长安的荔枝》,别人瞅着“一骑红尘妃子笑”只觉得*浪漫,他却盯着荔枝咋保鲜这难题。把历史掰开揉碎了找共鸣的能耐,难怪会觉得唐朝的张小敬,比老板还懂我。另一个把破除边界玩明白的,是香港导演林奕华。当年影视圈正火,随便拍个剧都容易火,但他偏要守着小剧场。他最拿手的,就是把《红楼梦》《西游记》这些老掉牙的经典,改成戳中现代人痛点的故事。**他改的《西游记》,不说啥西天取经的神话,反而演了唐僧师徒四人的现实破事儿。从夫妻吵架、师生矛盾,到选秀评审和选手的拉扯、导游跟游客的闹心,足足九九八十一种生活之难,全都是每天要面对的糟心事儿。他拍的《水浒传》,也不是啥江湖义气那套,九个男人征选黑帮电影演员的故事,演的全是现代人“被逼上梁山”的无奈,还有那些说不得的男人之罪。林奕华说,剧场的魔力就在于想象力没边儿。别人都想着一次成功、赶紧赚钱,他却把剧场当“种地”,慢慢播种、慢慢伺候,等着灵感**。不按别人的规矩活,才能活出步调。
《长安十二时辰》里**叫张小敬的女人,咋一看是个唐朝的死刑犯,可朋友圈里头,她倒成了心里头的“精神大哥”。就因为剧末那黑乎乎的画面里,她把个三品参将的官位撂那儿,拎着个破包就往西边跑,活脱脱一个没编制没身份的“社会闲散人员”。可偏偏就是这号人,让成堆的现代人跟着直点头,心里头喊:“要是我也能这么活该多好!”张小敬她理解的自由,可不是想躺着就躺着、想疯着就疯着那么简单。她非要揭穿**迷思:真要自由,那就是“不想干的事,你拦都拦不住”。这娘们儿,原先是个“不良帅”,守着长安城的三品官不做,非得当个游手好闲的“长安编外保安”,看着特轴,骨子里头最明白咋活人。这背后,藏着个叫以赛亚·柏林说的“积极自由”的道理。就是“自己说了算”:你让生活怎么揍你,脸都给你打肿了,可下一步往哪儿挪,**是你拿主意。张小敬查案一会儿帮着工匠,一会儿护着歌女,看着好像被一堆破事儿缠着,每一步都踩在自己认定的理儿上头。她心里头跟明镜一样:“家都坏了,不能不管,得修”,把寻常人放在心上的念想,比啥官印都更像成年人身上的勋章。反派龙波,那可就惨了。费了大半劲儿搞“暗杀计划”,到头才发现自己只是别人手里的件儿。更逗的是,真碰上皇帝了,立马就把以前的仇都给忘了,想着老老实实给朝廷当“打工崽”。他这哪叫自由?分明是被欲望跟别人的想法给牵着走,活成了自己最瞧不上的“工具人”。活脱脱跟一样,嘴上喊着“躺平”,转头又偷偷卷到半夜十二点,看着好像特有个性,早被那套规矩给捆死了。能把张小敬这么个“反常自由”写出来的,*就只有马伯庸这号“文学圈里头的拆盲盒高手”了。说出来你也许不信,《长安十二时辰》这想法,不是瞎编出来的,马伯庸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给整出来的。他在西安博物馆地底下那层,瞅见了个特大的长安沙盘,站在那儿往下一瞧,突然就来了劲儿,这剧的影子就这么出来了。马伯庸写历史有个核心套路,叫“创作无界”——不是瞎编,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老古董的事儿。就说张小敬历史上真有这么个人,但《安禄山事迹》里就一句话:他射杀了杨国忠。马伯庸倒是从这儿,抠出了一个“拼命护长安老百姓”的热血故事。为了让故事不跑偏,他翻遍了考古报告,连唐朝姑娘戴啥木簪都查得明明白白。但又没被老规矩给套住,直接用了24小时倒计时的节奏,把历史给写成古代版的反恐片,信息量密集得跟美剧一样,正中这些“刷手机刷到停不下来”的现代人下怀。这位曾经也是上班族的哥们儿最懂难处,好比他写《长安的荔枝》,别人瞅着“一骑红尘妃子笑”只觉得*浪漫,他却盯着荔枝咋保鲜这难题。把历史掰开揉碎了找共鸣的能耐,难怪会觉得唐朝的张小敬,比老板还懂我。另一个把破除边界玩明白的,是香港导演林奕华。当年影视圈正火,随便拍个剧都容易火,但他偏要守着小剧场。他最拿手的,就是把《红楼梦》《西游记》这些老掉牙的经典,改成戳中现代人痛点的故事。**他改的《西游记》,不说啥西天取经的神话,反而演了唐僧师徒四人的现实破事儿。从夫妻吵架、师生矛盾,到选秀评审和选手的拉扯、导游跟游客的闹心,足足九九八十一种生活之难,全都是每天要面对的糟心事儿。他拍的《水浒传》,也不是啥江湖义气那套,九个男人征选黑帮电影演员的故事,演的全是现代人“被逼上梁山”的无奈,还有那些说不得的男人之罪。林奕华说,剧场的魔力就在于想象力没边儿。别人都想着一次成功、赶紧赚钱,他却把剧场当“种地”,慢慢播种、慢慢伺候,等着灵感**。不按别人的规矩活,才能活出步调。
广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