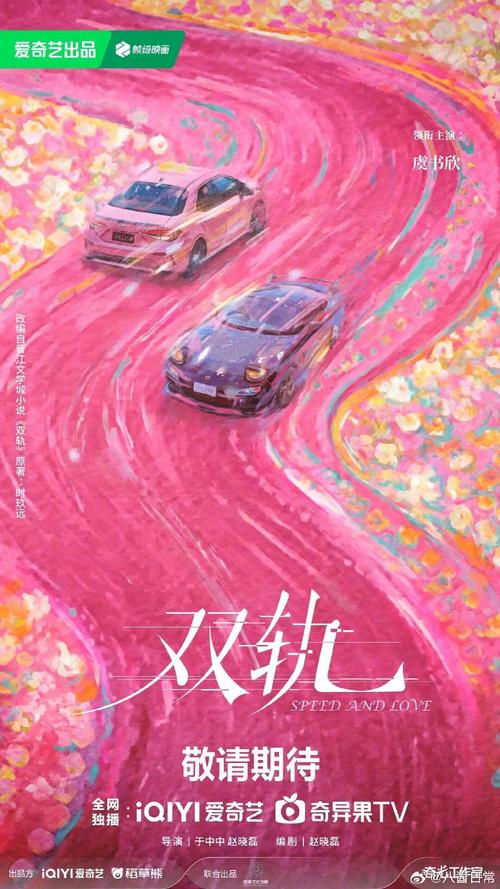燃比娃:李文愉的水墨动画处女作凭什么拿大奖?1. 水墨动画的“老古董”遇上新时代动画圈里,手绘水墨动画现在越来越少见,但李文愉的《燃比娃》偏偏是个特例。这部长片用最朴实的二维手绘,讲了一个羌族古老传说——猴形少年燃比娃追母、盗火、褪毛成人的故事。这可不是什么商业大片,技术不炫酷、故事不猎奇,但偏偏在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了个评委会大奖。评委夸它“水墨视觉系统尤为卓异”,说流动的墨迹在严寒中构建出“原始又诗性的神秘场域”。你可能会问:现在都啥年代了,为啥还有人玩这种“老土”的手绘?李文愉导演自己说:“我们本身就是创投出来的,再到西宁,这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回归。” 这部片子,既是他对动画语言的探索,也是对传统手法的坚守。2. 导演的“手稿情结”——几乎全片都是他亲手画《燃比娃》最扎心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帧都是李文愉亲手绘制、渲染完成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手稿,有铅笔线稿没擦干净,有水墨晕染的痕迹,还有他随手画的涂鸦。“我一直都想独立完成一部长片,”李文愉说,“之前在动画节看过国外有独立制作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一部长片也不是不可能。” 他不想用电脑制作,就想保留创作的“粗糙”质感。这种坚持有多苦?李文愉自己说:“最大的困难是我第一次做长片,整个制片流程比较难把控。以前做的都是短片,最多十来分钟,节奏进度的把控没有那么难,但长片是完全不同的体量。”更夸张的是,整部电影的职位表上,很多都写着“李文愉”。编剧、手稿绘制、整体制作……一个人扛下来,白天上课当大学老师,晚上回去画到凌晨两三点。3. 成长主题:从燃比娃到李文愉的自我投射《燃比娃》讲的是成长,但观众能明显感觉到,这其实是个导演的自我投射。片尾字幕里,他提到自己养了12年的狗,后来因为肿瘤去世。电影里,燃比娃的狗狗胸前有块红色伤疤,就是他家狗的影子。“其实整个影片就是投射了一段我自己的故事,”李文愉说,“毕业来到陌生的城市,很孤单,有时也很恐惧。当时我养了一条狗,它陪了我十二年。” 燃比娃从猴子进化成人,狗狗从狼变成犬,这两个进化对照,其实也是李文愉从一个人到独立导演的蜕变。电影里的“火种”象征着进化,但李文愉更想表达的,是“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他说:“电影里的那只怪兽就是恐惧的具象化,但实际上它是假的,根本不存在。燃比娃一开始不断逃避,到最后真正面对,结果发现恐惧是虚无的。”这种成长,既是燃比娃的,也是他自己的。4. 独立长片的快乐与代价做动画的人,往往都有些“轴”。李文愉就是这样,他坚持手绘,坚持个人化创作,甚至不惜熬夜、牺牲睡眠。但他说:“我负责的课程不是一个学期从头上到尾的,比如这门课集中授课三四周,那段时间里我的动画就稍微放放,专心上课,晚上回去再接着做。”这种矛盾,也是独立创作者的常态。你既要兼顾生活,又要追求艺术,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但李文愉似乎乐在其中:“做动画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很枯燥,我承认确实也有枯燥,但每个动画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些枯燥转化为快乐。”他最大的快乐,来自创作的不确定性。“比如一个画面做出来,其实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全新的感觉了,这种时刻就很快乐。”5. 水墨动画的未来:李文愉的坚持与探索《燃比娃》的成功,不仅是李文愉个人的胜利,也是水墨动画的一次回归。在这个特效当道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却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平衡,正是独立创作者的智慧。他们既想创新,又不想观众看不懂;既想保留自我,又想让更多人喜欢。《燃比娃》的获奖,或许只是开始。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文愉这样的动画人,用最朴素的手法,讲最动人的故事。---参考资料:1. FIRST青年电影展官网:《燃比娃》获奖公告2.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官网:《燃比娃》项目介绍3. 华沙电影节官网:《GotoCityELE》获奖记录4. 昂西国际动画节官网:《燃比娃》全球路演信息5. 柏林电影节官网:《燃比娃》入围新生代Kplus竞赛单元
燃比娃:李文愉的水墨动画处女作凭什么拿大奖?1. 水墨动画的“老古董”遇上新时代动画圈里,手绘水墨动画现在越来越少见,但李文愉的《燃比娃》偏偏是个特例。这部长片用最朴实的二维手绘,讲了一个羌族古老传说——猴形少年燃比娃追母、盗火、褪毛成人的故事。这可不是什么商业大片,技术不炫酷、故事不猎奇,但偏偏在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了个评委会大奖。评委夸它“水墨视觉系统尤为卓异”,说流动的墨迹在严寒中构建出“原始又诗性的神秘场域”。你可能会问:现在都啥年代了,为啥还有人玩这种“老土”的手绘?李文愉导演自己说:“我们本身就是创投出来的,再到西宁,这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回归。” 这部片子,既是他对动画语言的探索,也是对传统手法的坚守。2. 导演的“手稿情结”——几乎全片都是他亲手画《燃比娃》最扎心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帧都是李文愉亲手绘制、渲染完成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手稿,有铅笔线稿没擦干净,有水墨晕染的痕迹,还有他随手画的涂鸦。“我一直都想独立完成一部长片,”李文愉说,“之前在动画节看过国外有独立制作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一部长片也不是不可能。” 他不想用电脑制作,就想保留创作的“粗糙”质感。这种坚持有多苦?李文愉自己说:“最大的困难是我第一次做长片,整个制片流程比较难把控。以前做的都是短片,最多十来分钟,节奏进度的把控没有那么难,但长片是完全不同的体量。”更夸张的是,整部电影的职位表上,很多都写着“李文愉”。编剧、手稿绘制、整体制作……一个人扛下来,白天上课当大学老师,晚上回去画到凌晨两三点。3. 成长主题:从燃比娃到李文愉的自我投射《燃比娃》讲的是成长,但观众能明显感觉到,这其实是个导演的自我投射。片尾字幕里,他提到自己养了12年的狗,后来因为肿瘤去世。电影里,燃比娃的狗狗胸前有块红色伤疤,就是他家狗的影子。“其实整个影片就是投射了一段我自己的故事,”李文愉说,“毕业来到陌生的城市,很孤单,有时也很恐惧。当时我养了一条狗,它陪了我十二年。” 燃比娃从猴子进化成人,狗狗从狼变成犬,这两个进化对照,其实也是李文愉从一个人到独立导演的蜕变。电影里的“火种”象征着进化,但李文愉更想表达的,是“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他说:“电影里的那只怪兽就是恐惧的具象化,但实际上它是假的,根本不存在。燃比娃一开始不断逃避,到最后真正面对,结果发现恐惧是虚无的。”这种成长,既是燃比娃的,也是他自己的。4. 独立长片的快乐与代价做动画的人,往往都有些“轴”。李文愉就是这样,他坚持手绘,坚持个人化创作,甚至不惜熬夜、牺牲睡眠。但他说:“我负责的课程不是一个学期从头上到尾的,比如这门课集中授课三四周,那段时间里我的动画就稍微放放,专心上课,晚上回去再接着做。”这种矛盾,也是独立创作者的常态。你既要兼顾生活,又要追求艺术,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但李文愉似乎乐在其中:“做动画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很枯燥,我承认确实也有枯燥,但每个动画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些枯燥转化为快乐。”他最大的快乐,来自创作的不确定性。“比如一个画面做出来,其实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全新的感觉了,这种时刻就很快乐。”5. 水墨动画的未来:李文愉的坚持与探索《燃比娃》的成功,不仅是李文愉个人的胜利,也是水墨动画的一次回归。在这个特效当道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却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平衡,正是独立创作者的智慧。他们既想创新,又不想观众看不懂;既想保留自我,又想让更多人喜欢。《燃比娃》的获奖,或许只是开始。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文愉这样的动画人,用最朴素的手法,讲最动人的故事。---参考资料:1. FIRST青年电影展官网:《燃比娃》获奖公告2.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官网:《燃比娃》项目介绍3. 华沙电影节官网:《GotoCityELE》获奖记录4. 昂西国际动画节官网:《燃比娃》全球路演信息5. 柏林电影节官网:《燃比娃》入围新生代Kplus竞赛单元燃比娃 李文愉水墨动画处女作获大奖
 燃比娃:李文愉的水墨动画处女作凭什么拿大奖?1. 水墨动画的“老古董”遇上新时代动画圈里,手绘水墨动画现在越来越少见,但李文愉的《燃比娃》偏偏是个特例。这部长片用最朴实的二维手绘,讲了一个羌族古老传说——猴形少年燃比娃追母、盗火、褪毛成人的故事。这可不是什么商业大片,技术不炫酷、故事不猎奇,但偏偏在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了个评委会大奖。评委夸它“水墨视觉系统尤为卓异”,说流动的墨迹在严寒中构建出“原始又诗性的神秘场域”。你可能会问:现在都啥年代了,为啥还有人玩这种“老土”的手绘?李文愉导演自己说:“我们本身就是创投出来的,再到西宁,这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回归。” 这部片子,既是他对动画语言的探索,也是对传统手法的坚守。2. 导演的“手稿情结”——几乎全片都是他亲手画《燃比娃》最扎心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帧都是李文愉亲手绘制、渲染完成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手稿,有铅笔线稿没擦干净,有水墨晕染的痕迹,还有他随手画的涂鸦。“我一直都想独立完成一部长片,”李文愉说,“之前在动画节看过国外有独立制作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一部长片也不是不可能。” 他不想用电脑制作,就想保留创作的“粗糙”质感。这种坚持有多苦?李文愉自己说:“最大的困难是我第一次做长片,整个制片流程比较难把控。以前做的都是短片,最多十来分钟,节奏进度的把控没有那么难,但长片是完全不同的体量。”更夸张的是,整部电影的职位表上,很多都写着“李文愉”。编剧、手稿绘制、整体制作……一个人扛下来,白天上课当大学老师,晚上回去画到凌晨两三点。3. 成长主题:从燃比娃到李文愉的自我投射《燃比娃》讲的是成长,但观众能明显感觉到,这其实是个导演的自我投射。片尾字幕里,他提到自己养了12年的狗,后来因为肿瘤去世。电影里,燃比娃的狗狗胸前有块红色伤疤,就是他家狗的影子。“其实整个影片就是投射了一段我自己的故事,”李文愉说,“毕业来到陌生的城市,很孤单,有时也很恐惧。当时我养了一条狗,它陪了我十二年。” 燃比娃从猴子进化成人,狗狗从狼变成犬,这两个进化对照,其实也是李文愉从一个人到独立导演的蜕变。电影里的“火种”象征着进化,但李文愉更想表达的,是“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他说:“电影里的那只怪兽就是恐惧的具象化,但实际上它是假的,根本不存在。燃比娃一开始不断逃避,到最后真正面对,结果发现恐惧是虚无的。”这种成长,既是燃比娃的,也是他自己的。4. 独立长片的快乐与代价做动画的人,往往都有些“轴”。李文愉就是这样,他坚持手绘,坚持个人化创作,甚至不惜熬夜、牺牲睡眠。但他说:“我负责的课程不是一个学期从头上到尾的,比如这门课集中授课三四周,那段时间里我的动画就稍微放放,专心上课,晚上回去再接着做。”这种矛盾,也是独立创作者的常态。你既要兼顾生活,又要追求艺术,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但李文愉似乎乐在其中:“做动画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很枯燥,我承认确实也有枯燥,但每个动画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些枯燥转化为快乐。”他最大的快乐,来自创作的不确定性。“比如一个画面做出来,其实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全新的感觉了,这种时刻就很快乐。”5. 水墨动画的未来:李文愉的坚持与探索《燃比娃》的成功,不仅是李文愉个人的胜利,也是水墨动画的一次回归。在这个特效当道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却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平衡,正是独立创作者的智慧。他们既想创新,又不想观众看不懂;既想保留自我,又想让更多人喜欢。《燃比娃》的获奖,或许只是开始。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文愉这样的动画人,用最朴素的手法,讲最动人的故事。---参考资料:1. FIRST青年电影展官网:《燃比娃》获奖公告2.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官网:《燃比娃》项目介绍3. 华沙电影节官网:《GotoCityELE》获奖记录4. 昂西国际动画节官网:《燃比娃》全球路演信息5. 柏林电影节官网:《燃比娃》入围新生代Kplus竞赛单元
燃比娃:李文愉的水墨动画处女作凭什么拿大奖?1. 水墨动画的“老古董”遇上新时代动画圈里,手绘水墨动画现在越来越少见,但李文愉的《燃比娃》偏偏是个特例。这部长片用最朴实的二维手绘,讲了一个羌族古老传说——猴形少年燃比娃追母、盗火、褪毛成人的故事。这可不是什么商业大片,技术不炫酷、故事不猎奇,但偏偏在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了个评委会大奖。评委夸它“水墨视觉系统尤为卓异”,说流动的墨迹在严寒中构建出“原始又诗性的神秘场域”。你可能会问:现在都啥年代了,为啥还有人玩这种“老土”的手绘?李文愉导演自己说:“我们本身就是创投出来的,再到西宁,这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回归。” 这部片子,既是他对动画语言的探索,也是对传统手法的坚守。2. 导演的“手稿情结”——几乎全片都是他亲手画《燃比娃》最扎心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帧都是李文愉亲手绘制、渲染完成的。那些堆积如山的手稿,有铅笔线稿没擦干净,有水墨晕染的痕迹,还有他随手画的涂鸦。“我一直都想独立完成一部长片,”李文愉说,“之前在动画节看过国外有独立制作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一部长片也不是不可能。” 他不想用电脑制作,就想保留创作的“粗糙”质感。这种坚持有多苦?李文愉自己说:“最大的困难是我第一次做长片,整个制片流程比较难把控。以前做的都是短片,最多十来分钟,节奏进度的把控没有那么难,但长片是完全不同的体量。”更夸张的是,整部电影的职位表上,很多都写着“李文愉”。编剧、手稿绘制、整体制作……一个人扛下来,白天上课当大学老师,晚上回去画到凌晨两三点。3. 成长主题:从燃比娃到李文愉的自我投射《燃比娃》讲的是成长,但观众能明显感觉到,这其实是个导演的自我投射。片尾字幕里,他提到自己养了12年的狗,后来因为肿瘤去世。电影里,燃比娃的狗狗胸前有块红色伤疤,就是他家狗的影子。“其实整个影片就是投射了一段我自己的故事,”李文愉说,“毕业来到陌生的城市,很孤单,有时也很恐惧。当时我养了一条狗,它陪了我十二年。” 燃比娃从猴子进化成人,狗狗从狼变成犬,这两个进化对照,其实也是李文愉从一个人到独立导演的蜕变。电影里的“火种”象征着进化,但李文愉更想表达的,是“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他说:“电影里的那只怪兽就是恐惧的具象化,但实际上它是假的,根本不存在。燃比娃一开始不断逃避,到最后真正面对,结果发现恐惧是虚无的。”这种成长,既是燃比娃的,也是他自己的。4. 独立长片的快乐与代价做动画的人,往往都有些“轴”。李文愉就是这样,他坚持手绘,坚持个人化创作,甚至不惜熬夜、牺牲睡眠。但他说:“我负责的课程不是一个学期从头上到尾的,比如这门课集中授课三四周,那段时间里我的动画就稍微放放,专心上课,晚上回去再接着做。”这种矛盾,也是独立创作者的常态。你既要兼顾生活,又要追求艺术,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但李文愉似乎乐在其中:“做动画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很枯燥,我承认确实也有枯燥,但每个动画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些枯燥转化为快乐。”他最大的快乐,来自创作的不确定性。“比如一个画面做出来,其实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全新的感觉了,这种时刻就很快乐。”5. 水墨动画的未来:李文愉的坚持与探索《燃比娃》的成功,不仅是李文愉个人的胜利,也是水墨动画的一次回归。在这个特效当道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却走出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平衡,正是独立创作者的智慧。他们既想创新,又不想观众看不懂;既想保留自我,又想让更多人喜欢。《燃比娃》的获奖,或许只是开始。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文愉这样的动画人,用最朴素的手法,讲最动人的故事。---参考资料:1. FIRST青年电影展官网:《燃比娃》获奖公告2.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官网:《燃比娃》项目介绍3. 华沙电影节官网:《GotoCityELE》获奖记录4. 昂西国际动画节官网:《燃比娃》全球路演信息5. 柏林电影节官网:《燃比娃》入围新生代Kplus竞赛单元
广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