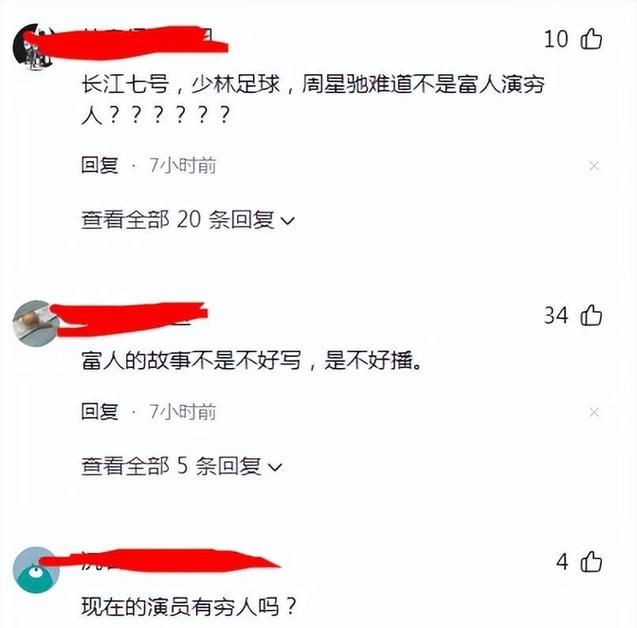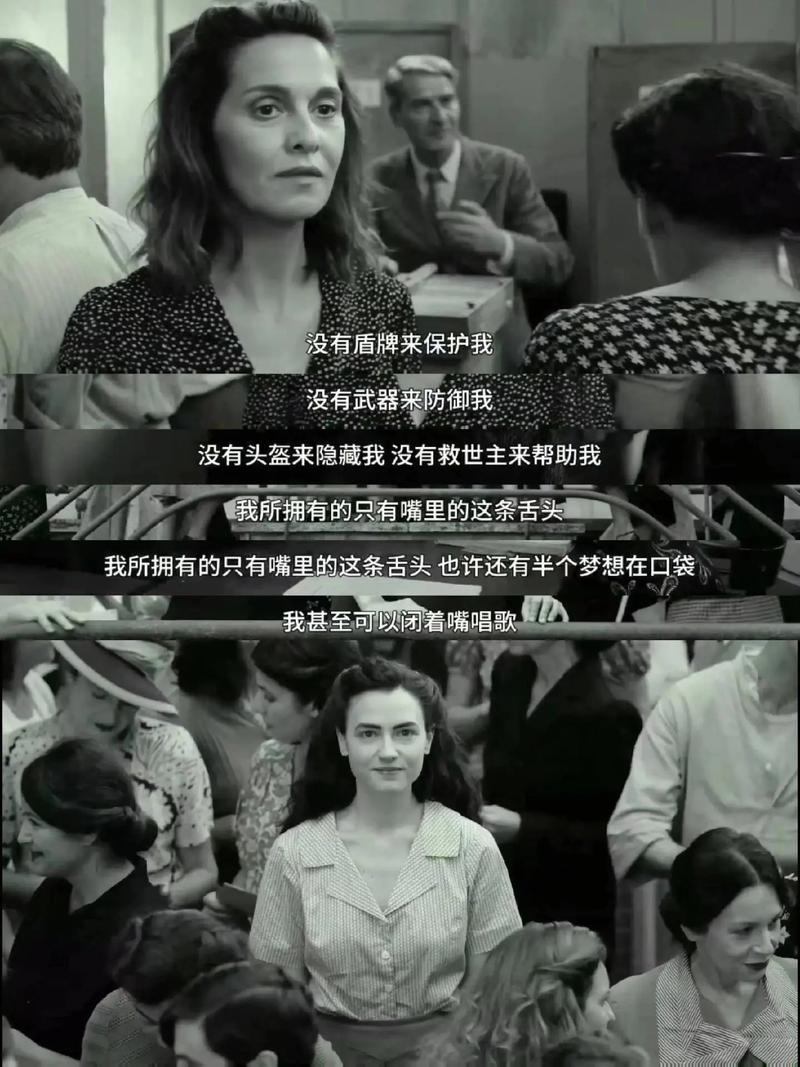《大风杀》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个最佳编剧奖,还得了个最佳男配角奖,算是挺出圈的片子了。这是中国第一部通过艺联专线搞长线放映的,挺。这电影看多了还有意思,影响挺广的,网上老有人写万字长文**,还有人做二创视频,把白客的“转型”当个重点聊。白客在这电影里,穿着灰西装、白衬衫,还有个灰百褶半裙,跟以前那个搞笑的王大锤不一样了,演的是个硬汉,孤胆英雄、敢跟人干架的角色。以前老演些“怂包”、“小职员”、“窝囊废”这类角色,变成“硬汉”、“拼命三郎”了。白客自己说,演戏就是他吃饭的家伙什,他不挑食,这是他在演艺圈混饭吃的道理。他以前演过王大锤,他觉得这是个**的例子。有人找他演类似的戏,他也不会想着要摆脱**形象,因为那碗饭就喂到他嘴边了,他会想好好吃这碗饭。白客话不多,但心里挺有数,主要是吐槽。他也承认,有时候也不想吃这碗饭,谁天天上班不憋屈也不会永远没点烦心事。生活里老有怨言,但要及时处理,及时和解。他说他和解能力强,总能想明白。《大风杀》的导演张琪找他白客已经演了十三年了,他从来没想过能吃这么久的饭,而且吃得精彩些,甚至觉得自己“还挺适合吃这碗饭”。他有挑剧本的余地了,但他挑的标准,跟火不火、热点没关系,也不管什么长远规划。他觉得导演能力、演员阵容好不好,不好判断,所以文本好看就成了他唯一的准绳。白客觉得,拍戏肯定得花钱,收入本身就是生意,总得有人沾点“铜臭味”,演员才能有点“单纯”。他谢谢这种保护,也愿意在规矩上让步。在澳门喜剧节上碰到偶像北野武先生,他很想问问看法,**被流程搞断了。《大风杀》是按心里想拍的,没拍“烂”,就是拍成了白客没想过的样子。跟导演张琪沟通白客脑子里一直按文艺片的样子想画面,第一次看到成片,他挺吃惊的。这电影**超出他的想象,近几年院线里也少见。他惊讶于这电影的商业性、武侠味、戏剧性、现实感、虚幻感,还有实实在在的人物关系。电影里,三个警察,一把枪,四十三个穿着盔甲的悍匪,打了一场不赢的仗,**打赢了。导演在个人风格很强的表达下,把节奏拿捏得死死的,观赏性足,对生命和未来提出了问题。夏然一个人坐上开往深圳的巴士,一切好像都清楚了,但镜头对准夏然观众会马上知道没那么简单。白客用眼神演出了全片一以贯之的紧张,还有夏然的迷茫,好像心里还有风沙在翻腾。白客演的角色大多是普通人,就算夏然这种在最关紧要的部分时刻能救场的角色,也只是“特殊一点儿的普通人”。他对个人英雄主义没啥兴趣,也不喜欢主角光环。这些角色看不到上帝视角,更没法给自己安排什么高湖,最的就是被生活的浪潮给掀翻,翻一次又一次。面对着命运,白客不做计划,他觉得一切都转瞬即逝,他**接受演艺事业说停就停,也能接受生命说没就没。他觉得,就跟着浪潮走呗,看它要把我推到哪儿,咱能做的只有好好做人。人生就是不用太较真,在**说不清道不明世界里,不用太较真就是你有数的**,你要是企图控制世界、控制人生,那你就有点没数了。所以白客经常干的事,就是把“升华”的表演“往回拽”。当身心都投入角色里,设身处地,角色只会想着怎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不会想着这时候身上要亮起什么光芒。他常陷在角色里,不明白为啥要承受这些,但有时候也会琢磨琢磨**事儿,不去“升华”的话,表演就太淡了。影视作品想抓住观众,故事得跌宕起伏,节奏得张弛有度,白客知道了这点,也试着调整。虽然是喜剧演员出身,但白客近几年接喜剧角色谨慎,《年会不能停!》也是纠结了好久才决定演。他真有点怵,因为没跟大鹏合作过,很多东西之所以牛,就是因为它没发生。一旦他们合作了,现实就会坍塌成一条线,就只有一种**了。好在薛定谔的箱子打开了,猫活着,这给白客演《长安的荔枝》打了信心。白客始终觉得拍喜剧,是要从头到尾都高兴(演员的快乐)。要是拍个喜剧,每天都被吐槽,过得特痛苦,就算他最后理解了导演要啥,给了,戏**了,他也不太会看这戏,也不会感激这段痛苦,就算从业务上讲他学到了不少。你生产的是快乐的东西,里面有很多苦涩,**喜剧本身就不纯粹了。白客觉得,喜剧难就难在连学校*没法教,没人能教出一个固定模式,说严格按照**模式演,观众开心。不会演戏的人有时候反而能演好戏,很难说。演员不是纯技术行业,虽然它有标准,大家最好不要互相理解,互相理解了,不就都一样了?就得这么着才有意思。白客觉得**世界的底色挺荒诞的,所有人看着同一个世界,看到的却都不一样。有的人特严肃地看,有的人解构地看,然后你就发现人生的滋味出来了。和平年代,享受自己这样看,也允许别人那样看,活得有滋味、有意思就是活得有意义了。
《大风杀》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个最佳编剧奖,还得了个最佳男配角奖,算是挺出圈的片子了。这是中国第一部通过艺联专线搞长线放映的,挺。这电影看多了还有意思,影响挺广的,网上老有人写万字长文**,还有人做二创视频,把白客的“转型”当个重点聊。白客在这电影里,穿着灰西装、白衬衫,还有个灰百褶半裙,跟以前那个搞笑的王大锤不一样了,演的是个硬汉,孤胆英雄、敢跟人干架的角色。以前老演些“怂包”、“小职员”、“窝囊废”这类角色,变成“硬汉”、“拼命三郎”了。白客自己说,演戏就是他吃饭的家伙什,他不挑食,这是他在演艺圈混饭吃的道理。他以前演过王大锤,他觉得这是个**的例子。有人找他演类似的戏,他也不会想着要摆脱**形象,因为那碗饭就喂到他嘴边了,他会想好好吃这碗饭。白客话不多,但心里挺有数,主要是吐槽。他也承认,有时候也不想吃这碗饭,谁天天上班不憋屈也不会永远没点烦心事。生活里老有怨言,但要及时处理,及时和解。他说他和解能力强,总能想明白。《大风杀》的导演张琪找他白客已经演了十三年了,他从来没想过能吃这么久的饭,而且吃得精彩些,甚至觉得自己“还挺适合吃这碗饭”。他有挑剧本的余地了,但他挑的标准,跟火不火、热点没关系,也不管什么长远规划。他觉得导演能力、演员阵容好不好,不好判断,所以文本好看就成了他唯一的准绳。白客觉得,拍戏肯定得花钱,收入本身就是生意,总得有人沾点“铜臭味”,演员才能有点“单纯”。他谢谢这种保护,也愿意在规矩上让步。在澳门喜剧节上碰到偶像北野武先生,他很想问问看法,**被流程搞断了。《大风杀》是按心里想拍的,没拍“烂”,就是拍成了白客没想过的样子。跟导演张琪沟通白客脑子里一直按文艺片的样子想画面,第一次看到成片,他挺吃惊的。这电影**超出他的想象,近几年院线里也少见。他惊讶于这电影的商业性、武侠味、戏剧性、现实感、虚幻感,还有实实在在的人物关系。电影里,三个警察,一把枪,四十三个穿着盔甲的悍匪,打了一场不赢的仗,**打赢了。导演在个人风格很强的表达下,把节奏拿捏得死死的,观赏性足,对生命和未来提出了问题。夏然一个人坐上开往深圳的巴士,一切好像都清楚了,但镜头对准夏然观众会马上知道没那么简单。白客用眼神演出了全片一以贯之的紧张,还有夏然的迷茫,好像心里还有风沙在翻腾。白客演的角色大多是普通人,就算夏然这种在最关紧要的部分时刻能救场的角色,也只是“特殊一点儿的普通人”。他对个人英雄主义没啥兴趣,也不喜欢主角光环。这些角色看不到上帝视角,更没法给自己安排什么高湖,最的就是被生活的浪潮给掀翻,翻一次又一次。面对着命运,白客不做计划,他觉得一切都转瞬即逝,他**接受演艺事业说停就停,也能接受生命说没就没。他觉得,就跟着浪潮走呗,看它要把我推到哪儿,咱能做的只有好好做人。人生就是不用太较真,在**说不清道不明世界里,不用太较真就是你有数的**,你要是企图控制世界、控制人生,那你就有点没数了。所以白客经常干的事,就是把“升华”的表演“往回拽”。当身心都投入角色里,设身处地,角色只会想着怎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不会想着这时候身上要亮起什么光芒。他常陷在角色里,不明白为啥要承受这些,但有时候也会琢磨琢磨**事儿,不去“升华”的话,表演就太淡了。影视作品想抓住观众,故事得跌宕起伏,节奏得张弛有度,白客知道了这点,也试着调整。虽然是喜剧演员出身,但白客近几年接喜剧角色谨慎,《年会不能停!》也是纠结了好久才决定演。他真有点怵,因为没跟大鹏合作过,很多东西之所以牛,就是因为它没发生。一旦他们合作了,现实就会坍塌成一条线,就只有一种**了。好在薛定谔的箱子打开了,猫活着,这给白客演《长安的荔枝》打了信心。白客始终觉得拍喜剧,是要从头到尾都高兴(演员的快乐)。要是拍个喜剧,每天都被吐槽,过得特痛苦,就算他最后理解了导演要啥,给了,戏**了,他也不太会看这戏,也不会感激这段痛苦,就算从业务上讲他学到了不少。你生产的是快乐的东西,里面有很多苦涩,**喜剧本身就不纯粹了。白客觉得,喜剧难就难在连学校*没法教,没人能教出一个固定模式,说严格按照**模式演,观众开心。不会演戏的人有时候反而能演好戏,很难说。演员不是纯技术行业,虽然它有标准,大家最好不要互相理解,互相理解了,不就都一样了?就得这么着才有意思。白客觉得**世界的底色挺荒诞的,所有人看着同一个世界,看到的却都不一样。有的人特严肃地看,有的人解构地看,然后你就发现人生的滋味出来了。和平年代,享受自己这样看,也允许别人那样看,活得有滋味、有意思就是活得有意义了。《大风杀》获奖 白客演技获赞 不挑饭的实用派演员
 《大风杀》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个最佳编剧奖,还得了个最佳男配角奖,算是挺出圈的片子了。这是中国第一部通过艺联专线搞长线放映的,挺。这电影看多了还有意思,影响挺广的,网上老有人写万字长文**,还有人做二创视频,把白客的“转型”当个重点聊。白客在这电影里,穿着灰西装、白衬衫,还有个灰百褶半裙,跟以前那个搞笑的王大锤不一样了,演的是个硬汉,孤胆英雄、敢跟人干架的角色。以前老演些“怂包”、“小职员”、“窝囊废”这类角色,变成“硬汉”、“拼命三郎”了。白客自己说,演戏就是他吃饭的家伙什,他不挑食,这是他在演艺圈混饭吃的道理。他以前演过王大锤,他觉得这是个**的例子。有人找他演类似的戏,他也不会想着要摆脱**形象,因为那碗饭就喂到他嘴边了,他会想好好吃这碗饭。白客话不多,但心里挺有数,主要是吐槽。他也承认,有时候也不想吃这碗饭,谁天天上班不憋屈也不会永远没点烦心事。生活里老有怨言,但要及时处理,及时和解。他说他和解能力强,总能想明白。《大风杀》的导演张琪找他白客已经演了十三年了,他从来没想过能吃这么久的饭,而且吃得精彩些,甚至觉得自己“还挺适合吃这碗饭”。他有挑剧本的余地了,但他挑的标准,跟火不火、热点没关系,也不管什么长远规划。他觉得导演能力、演员阵容好不好,不好判断,所以文本好看就成了他唯一的准绳。白客觉得,拍戏肯定得花钱,收入本身就是生意,总得有人沾点“铜臭味”,演员才能有点“单纯”。他谢谢这种保护,也愿意在规矩上让步。在澳门喜剧节上碰到偶像北野武先生,他很想问问看法,**被流程搞断了。《大风杀》是按心里想拍的,没拍“烂”,就是拍成了白客没想过的样子。跟导演张琪沟通白客脑子里一直按文艺片的样子想画面,第一次看到成片,他挺吃惊的。这电影**超出他的想象,近几年院线里也少见。他惊讶于这电影的商业性、武侠味、戏剧性、现实感、虚幻感,还有实实在在的人物关系。电影里,三个警察,一把枪,四十三个穿着盔甲的悍匪,打了一场不赢的仗,**打赢了。导演在个人风格很强的表达下,把节奏拿捏得死死的,观赏性足,对生命和未来提出了问题。夏然一个人坐上开往深圳的巴士,一切好像都清楚了,但镜头对准夏然观众会马上知道没那么简单。白客用眼神演出了全片一以贯之的紧张,还有夏然的迷茫,好像心里还有风沙在翻腾。白客演的角色大多是普通人,就算夏然这种在最关紧要的部分时刻能救场的角色,也只是“特殊一点儿的普通人”。他对个人英雄主义没啥兴趣,也不喜欢主角光环。这些角色看不到上帝视角,更没法给自己安排什么高湖,最的就是被生活的浪潮给掀翻,翻一次又一次。面对着命运,白客不做计划,他觉得一切都转瞬即逝,他**接受演艺事业说停就停,也能接受生命说没就没。他觉得,就跟着浪潮走呗,看它要把我推到哪儿,咱能做的只有好好做人。人生就是不用太较真,在**说不清道不明世界里,不用太较真就是你有数的**,你要是企图控制世界、控制人生,那你就有点没数了。所以白客经常干的事,就是把“升华”的表演“往回拽”。当身心都投入角色里,设身处地,角色只会想着怎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不会想着这时候身上要亮起什么光芒。他常陷在角色里,不明白为啥要承受这些,但有时候也会琢磨琢磨**事儿,不去“升华”的话,表演就太淡了。影视作品想抓住观众,故事得跌宕起伏,节奏得张弛有度,白客知道了这点,也试着调整。虽然是喜剧演员出身,但白客近几年接喜剧角色谨慎,《年会不能停!》也是纠结了好久才决定演。他真有点怵,因为没跟大鹏合作过,很多东西之所以牛,就是因为它没发生。一旦他们合作了,现实就会坍塌成一条线,就只有一种**了。好在薛定谔的箱子打开了,猫活着,这给白客演《长安的荔枝》打了信心。白客始终觉得拍喜剧,是要从头到尾都高兴(演员的快乐)。要是拍个喜剧,每天都被吐槽,过得特痛苦,就算他最后理解了导演要啥,给了,戏**了,他也不太会看这戏,也不会感激这段痛苦,就算从业务上讲他学到了不少。你生产的是快乐的东西,里面有很多苦涩,**喜剧本身就不纯粹了。白客觉得,喜剧难就难在连学校*没法教,没人能教出一个固定模式,说严格按照**模式演,观众开心。不会演戏的人有时候反而能演好戏,很难说。演员不是纯技术行业,虽然它有标准,大家最好不要互相理解,互相理解了,不就都一样了?就得这么着才有意思。白客觉得**世界的底色挺荒诞的,所有人看着同一个世界,看到的却都不一样。有的人特严肃地看,有的人解构地看,然后你就发现人生的滋味出来了。和平年代,享受自己这样看,也允许别人那样看,活得有滋味、有意思就是活得有意义了。
《大风杀》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个最佳编剧奖,还得了个最佳男配角奖,算是挺出圈的片子了。这是中国第一部通过艺联专线搞长线放映的,挺。这电影看多了还有意思,影响挺广的,网上老有人写万字长文**,还有人做二创视频,把白客的“转型”当个重点聊。白客在这电影里,穿着灰西装、白衬衫,还有个灰百褶半裙,跟以前那个搞笑的王大锤不一样了,演的是个硬汉,孤胆英雄、敢跟人干架的角色。以前老演些“怂包”、“小职员”、“窝囊废”这类角色,变成“硬汉”、“拼命三郎”了。白客自己说,演戏就是他吃饭的家伙什,他不挑食,这是他在演艺圈混饭吃的道理。他以前演过王大锤,他觉得这是个**的例子。有人找他演类似的戏,他也不会想着要摆脱**形象,因为那碗饭就喂到他嘴边了,他会想好好吃这碗饭。白客话不多,但心里挺有数,主要是吐槽。他也承认,有时候也不想吃这碗饭,谁天天上班不憋屈也不会永远没点烦心事。生活里老有怨言,但要及时处理,及时和解。他说他和解能力强,总能想明白。《大风杀》的导演张琪找他白客已经演了十三年了,他从来没想过能吃这么久的饭,而且吃得精彩些,甚至觉得自己“还挺适合吃这碗饭”。他有挑剧本的余地了,但他挑的标准,跟火不火、热点没关系,也不管什么长远规划。他觉得导演能力、演员阵容好不好,不好判断,所以文本好看就成了他唯一的准绳。白客觉得,拍戏肯定得花钱,收入本身就是生意,总得有人沾点“铜臭味”,演员才能有点“单纯”。他谢谢这种保护,也愿意在规矩上让步。在澳门喜剧节上碰到偶像北野武先生,他很想问问看法,**被流程搞断了。《大风杀》是按心里想拍的,没拍“烂”,就是拍成了白客没想过的样子。跟导演张琪沟通白客脑子里一直按文艺片的样子想画面,第一次看到成片,他挺吃惊的。这电影**超出他的想象,近几年院线里也少见。他惊讶于这电影的商业性、武侠味、戏剧性、现实感、虚幻感,还有实实在在的人物关系。电影里,三个警察,一把枪,四十三个穿着盔甲的悍匪,打了一场不赢的仗,**打赢了。导演在个人风格很强的表达下,把节奏拿捏得死死的,观赏性足,对生命和未来提出了问题。夏然一个人坐上开往深圳的巴士,一切好像都清楚了,但镜头对准夏然观众会马上知道没那么简单。白客用眼神演出了全片一以贯之的紧张,还有夏然的迷茫,好像心里还有风沙在翻腾。白客演的角色大多是普通人,就算夏然这种在最关紧要的部分时刻能救场的角色,也只是“特殊一点儿的普通人”。他对个人英雄主义没啥兴趣,也不喜欢主角光环。这些角色看不到上帝视角,更没法给自己安排什么高湖,最的就是被生活的浪潮给掀翻,翻一次又一次。面对着命运,白客不做计划,他觉得一切都转瞬即逝,他**接受演艺事业说停就停,也能接受生命说没就没。他觉得,就跟着浪潮走呗,看它要把我推到哪儿,咱能做的只有好好做人。人生就是不用太较真,在**说不清道不明世界里,不用太较真就是你有数的**,你要是企图控制世界、控制人生,那你就有点没数了。所以白客经常干的事,就是把“升华”的表演“往回拽”。当身心都投入角色里,设身处地,角色只会想着怎么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不会想着这时候身上要亮起什么光芒。他常陷在角色里,不明白为啥要承受这些,但有时候也会琢磨琢磨**事儿,不去“升华”的话,表演就太淡了。影视作品想抓住观众,故事得跌宕起伏,节奏得张弛有度,白客知道了这点,也试着调整。虽然是喜剧演员出身,但白客近几年接喜剧角色谨慎,《年会不能停!》也是纠结了好久才决定演。他真有点怵,因为没跟大鹏合作过,很多东西之所以牛,就是因为它没发生。一旦他们合作了,现实就会坍塌成一条线,就只有一种**了。好在薛定谔的箱子打开了,猫活着,这给白客演《长安的荔枝》打了信心。白客始终觉得拍喜剧,是要从头到尾都高兴(演员的快乐)。要是拍个喜剧,每天都被吐槽,过得特痛苦,就算他最后理解了导演要啥,给了,戏**了,他也不太会看这戏,也不会感激这段痛苦,就算从业务上讲他学到了不少。你生产的是快乐的东西,里面有很多苦涩,**喜剧本身就不纯粹了。白客觉得,喜剧难就难在连学校*没法教,没人能教出一个固定模式,说严格按照**模式演,观众开心。不会演戏的人有时候反而能演好戏,很难说。演员不是纯技术行业,虽然它有标准,大家最好不要互相理解,互相理解了,不就都一样了?就得这么着才有意思。白客觉得**世界的底色挺荒诞的,所有人看着同一个世界,看到的却都不一样。有的人特严肃地看,有的人解构地看,然后你就发现人生的滋味出来了。和平年代,享受自己这样看,也允许别人那样看,活得有滋味、有意思就是活得有意义了。
广告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