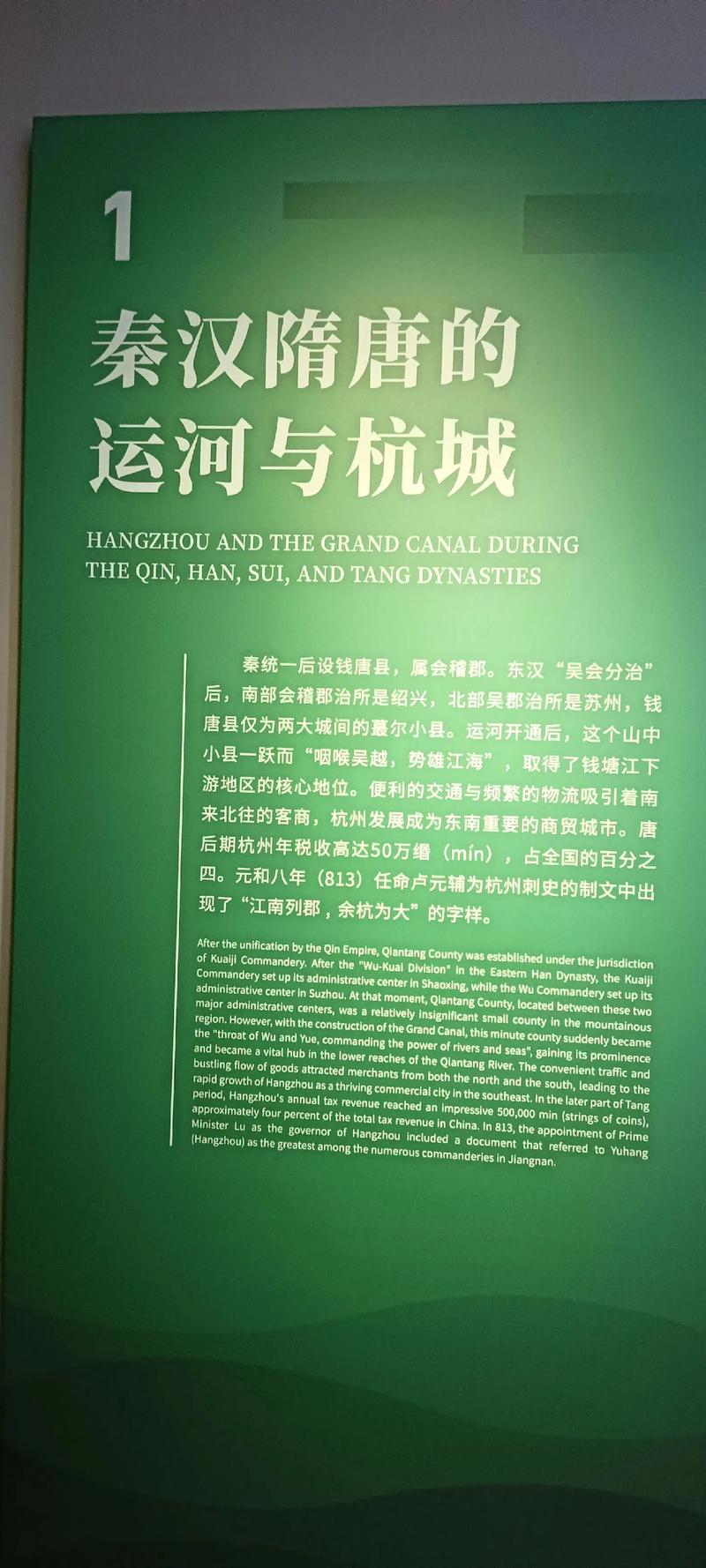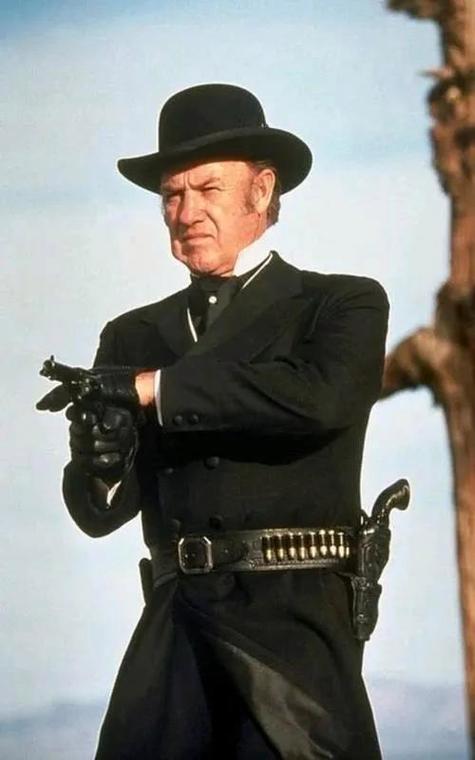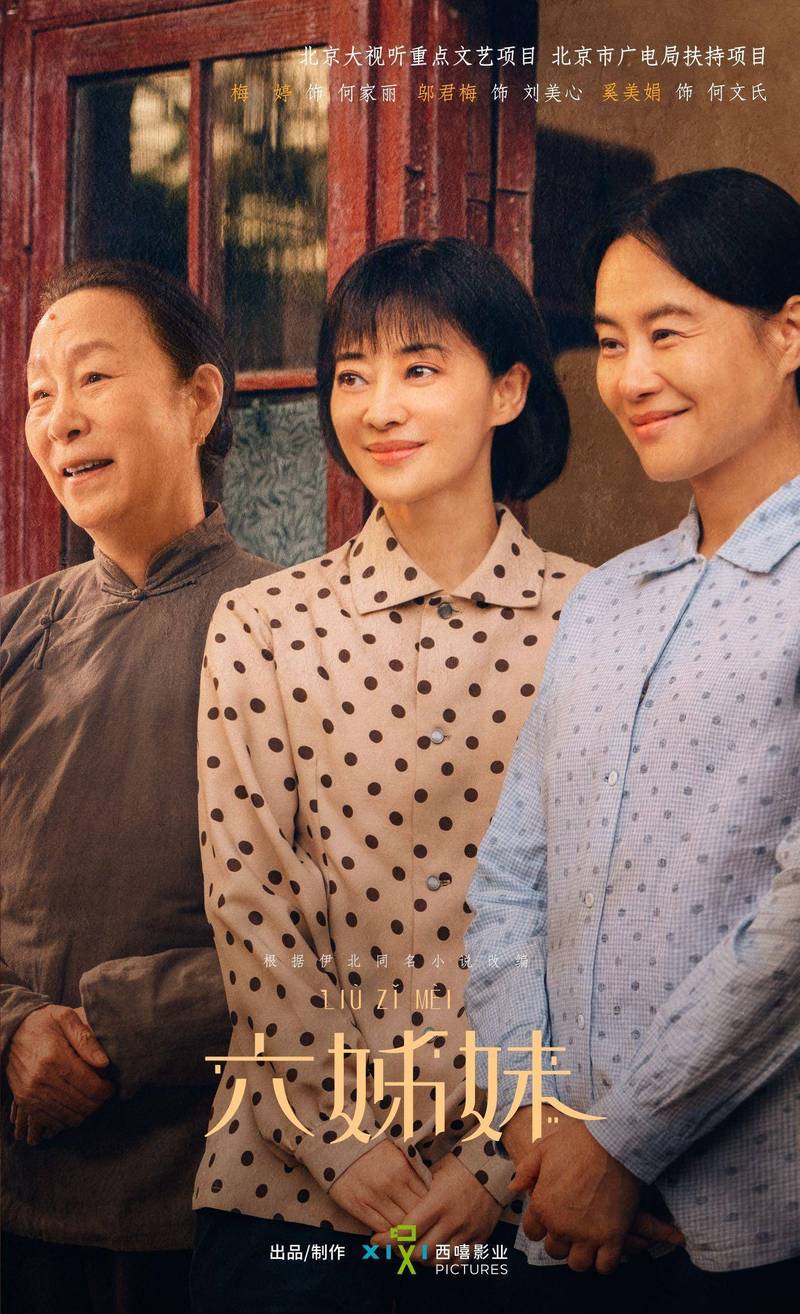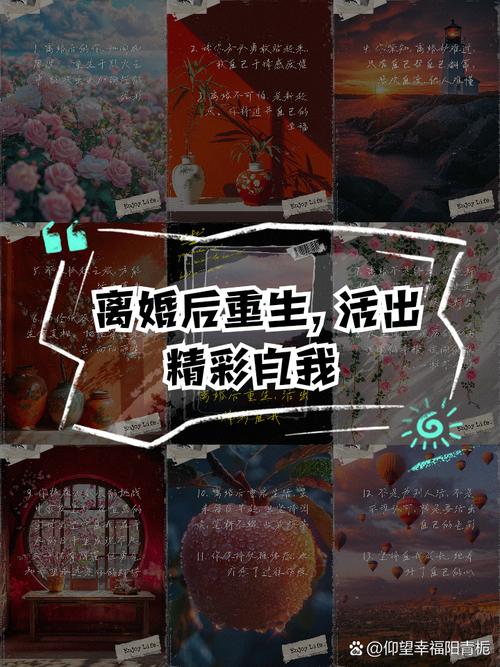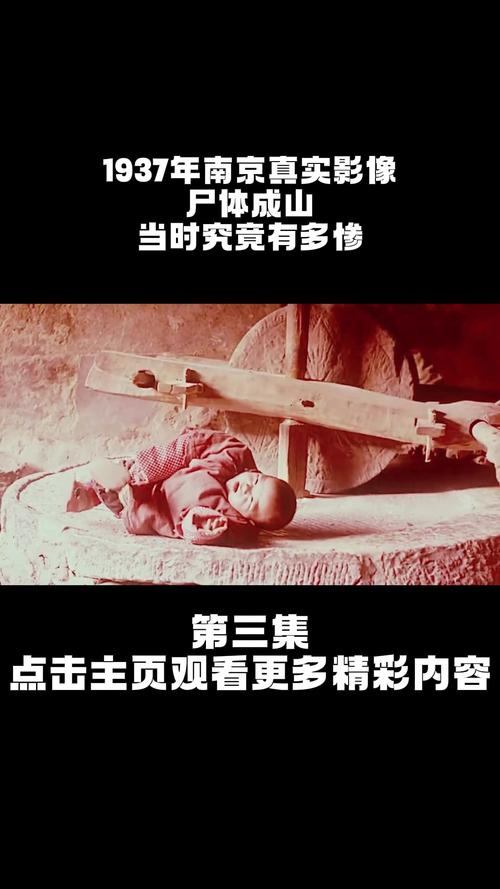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豆瓣上打出了8.6分,今年夏天算是个爆款了。故事是这么回事,当年日军有个随军摄影师叫伊藤秀夫,他想着拍点显摆日军威风的照片,就找到了南京一家叫吉祥照相馆的。**没想到,这些老百姓因为洗照片,反而躲过一劫。照片洗出来伊藤秀夫慢慢发现,日军那些干的事儿可一点都不威风。杀人、强奸、抢东西,这些血腥场面电影里都*直白地***,看得人心里直发毛。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这种手,那罪可就大了去了。可战后要给这些罪责定个谱,事情还真不那么容易办。电影里说了,战后有些日军内部就搞这套,说他们是忠于天皇,把杀人这些事儿说得好**为民除害一样。到了战后法庭上,那些战犯还死不认账,说要不是中国军队早跑了,南京老百姓哪会遭罪?要不是南京几位市民留了那些照片作证,这些日本战犯指不定就真脱罪了呢?要说这追查正义的事儿,不光是亚洲,欧洲那边对纳粹的审判,也是一场*漫长的“搞正义”的社会实验。这场实验持续了小几十年,全为啥追查正义会这么难。谁是受害者?谁该受罚?什么样的罚才算合适?这些问题都*模糊,没有标准答案。玛丽·弗尔布鲁克写的《大清算》里就说了,这场审判*费劲的,*暧昧的,破除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审判里,“正义”**概念会变的,不同国家、对不同人,正义就不一样。有些罪大恶极的,反而被轻易放过了;有些人又***远超他们过错的惩罚。这场本想搞“正义”的审判,最后反而成了政治、利益拉扯的复杂游戏。1963年到1965年,法兰克福开了个审奥斯维辛的庭,这庭在德国人眼里,算是他们“面对历史”的一个标志。这主要是因为奥斯维辛太重要了,审判过程中揭的罪行也太吓人了。审判发起者的目标也*明确的,就是要整个大规模灭绝的系统上法庭,不光是审几个个体。在媒体上***凶,大家看法也两极分化。在非犹太学者和普通读者里,纳粹大屠杀的地位算是确立了。可要说司法清算上,奥斯维辛这审判反倒说明了,这种事儿想办成,太难了。

要往法庭上对一个大规模杀人的系统下判决,几乎不**。一个国家发动、支持这种集体暴力,还让普通人跟着掺和进来,要用个体罪责去审,那**难上加难。《纽伦堡:纳粹战犯在审判》里就说了,奥斯维辛那会儿,光党卫队队员就有八千多名,女性守卫也有两百多个,这些人在西德受审的没几人,剩下的大多没上过法庭。法兰克福这审奥斯维辛的庭,检察官挑被告的时候也*费劲的,得选那些他们觉得最能定罪的人。不光要考虑被告在集中营系统里干啥,还得挑那些容易被揪出来,又能显出凶手的残忍和虐待的。这些被告在德国叫“作案人”(Täter),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干这些事儿没动过脑子,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么说跟事儿没多大关系,对实际发生的事儿不太清楚,不负责杀人的事儿,就是听命令,不听命令就得遭殃。审判里,有些证人遭的罪也不小,尤其有个叫汉斯·拉特恩泽尔的辩护律师,手段*狠的。他经常拿证人记不清日期啊什么的开玩笑,暗示证人是在撒谎。辩护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把被告说成是“希特勒的受害者”。1965年8月20日,审判长汉斯·霍夫迈耶(HansHofmeyer)念完判决书,这审就结束了。***德国已经不用死刑了,所以判决里*没人判死刑。在20个被告里,只有6人判了终身监禁,10个人判了3.5年到14年的刑,有个小时候就参与进来的,按未成年人的规矩判,还有3个因为证据不够,判了无罪。审判快结束时,西比尔·贝德福德说,**法官霍夫迈耶博士,平时*稳的,能让法庭保持冷静,可审完之后,他自己却崩溃了。要是单看把干坏事的人绳之以法,这***失望的。按罪行看,好多判决都*轻的,再说,要运转奥斯维辛,光是要6000到8000人,实际被判的才17人。鲍尔确实把奥斯维辛给闹大了,可离他想的正义差得远。在这过程中,他也觉得,反对他的人*多,离开办公室都觉得自己像在“敌人的地盘上”。赔偿,那也是另一回事了。受害者想拿点补偿,**被拒,或者给的数目太小,觉得*没劲的。可那些当年跟着希特勒干活的公务员、法官、医生啥的,战后继续干,还能拿高工资、拿全额退休金。这种事儿一出来,不公正的感觉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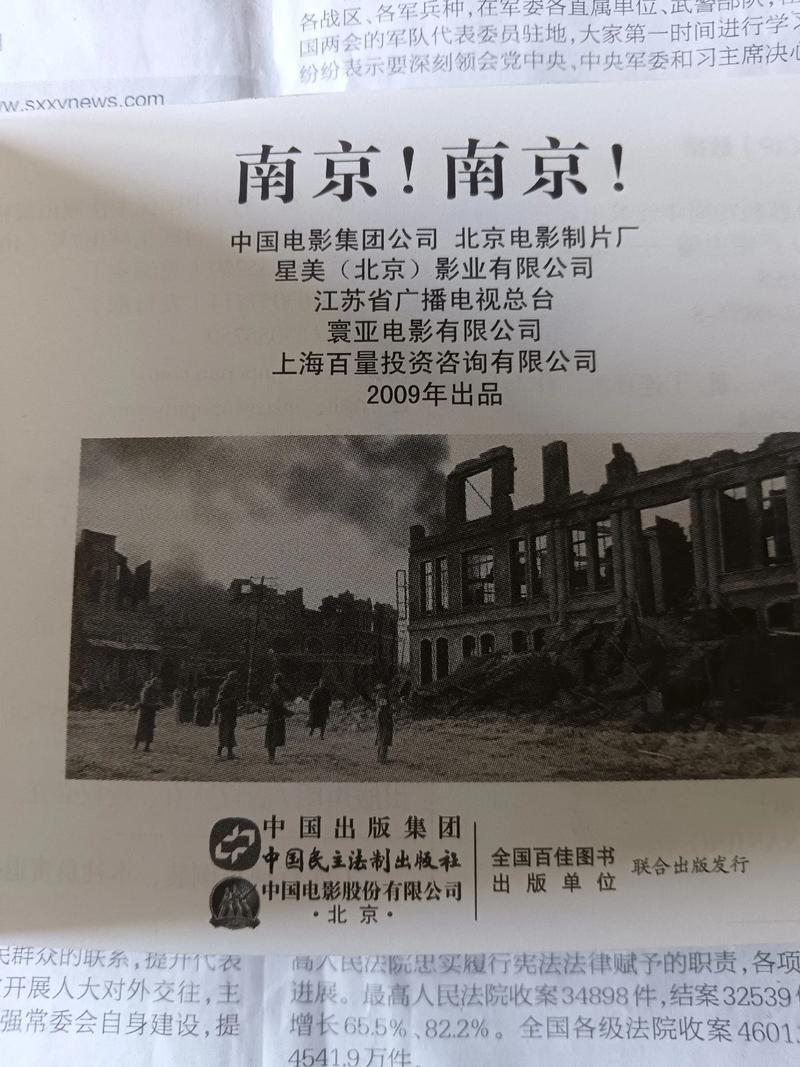
毫无疑问,啥措施也弥补不了纳粹的罪过,也救不回那些死的人。幸存者要的赔偿,跟他们受的苦比起来,确实差远了,可要拿到这笔钱,也难。那些管发补偿的人,跟以前政府关系**还*好。还存在其他不公平,**有些幸存者组织得厉害,有些群体就被忽视了,**还有偏见啥的,政治环境、舆论风向也影响事儿。在第三帝国的继承国里,没哪个国家给所有受害者全补偿。民主德国把国家社会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不愿意承认自己欠补偿。苏联主要想拿点钱来重建,从东德弄了不少东西。奥地利也不愿意给,想搞个“奥地利”民族身份,不想想起以前的事。后继政府和老百姓都*不想承认自己得补偿受害者的。因为纳粹的“罪”在法律上被说成是集中营守卫的虐待,所以能要求赔偿的受害者就少了。汉斯·弗兰肯塔尔说,他和弟弟在I.G.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当奴隶劳工,总共只拿到了1万马克,补偿工厂把他们当奴隶,补偿当局把他们遣送,补偿他们失去的青春、在集中营的遭遇、亲人没了,还有一辈子身体心理问题。有些群体的歧视没断,**“反社会人士”或“罪犯”那些人。反吉卜赛政策在战后德国还实行着,好多官员当年就“处理”过罗姆人和辛提人,还是那套看法。用这点钱来摆脱责任,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就是靠**。在50年代,德国政府站在道德高地上,那些大罪没受到实际惩罚,反而躲在个“责任”的幌子后面。给剩下的幸存者这点钱,是巩固了德国能面对过去的名声,但*没真解决罪责问题。**进步是有的,但即便是参与要赔偿、建立“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的人,也承认这迟来的正义不完整。痛苦、磨难和不公正的档案、证言、口供,好像永远也翻不完。那些司法调查、幸存者的痛苦证言,对司法正义没啥用了,只能当历史资料。若干坏事的人基本上都逃了惩罚,那只有无辜的人会继续受苦。就算他们等到上法庭那天,那也**不是个好地方。清算过去是个大故事,审判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家更多精力用在家人朋友邻里之间的瓜,或者自己写回忆录啥的,比法庭上的对抗还多。私下清算不像法庭判决那么清楚,是个没明确目标、总变来变去的过程。“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得改改了。深度追踪对施暴者的审判和反思,看“制度之恶”怎么操控“弱点”达成集体暴力。在伤痛慢慢淡了得再听听幸存者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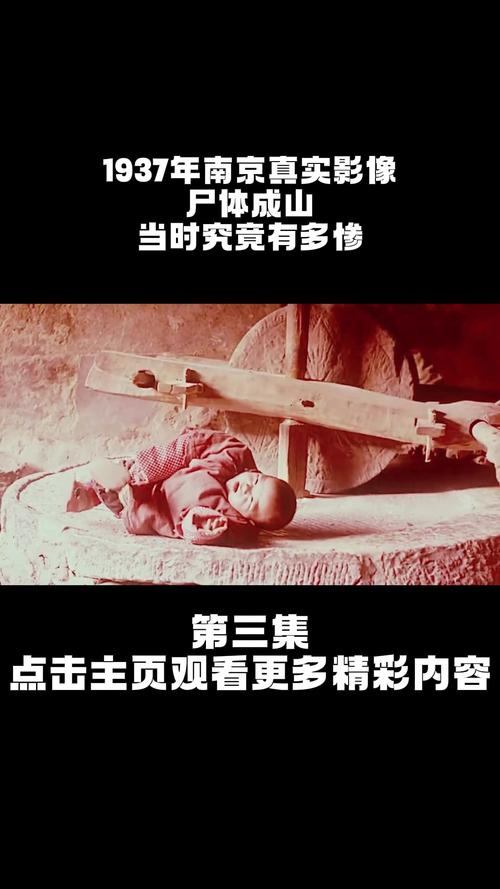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豆瓣上打出了8.6分,今年夏天算是个爆款了。故事是这么回事,当年日军有个随军摄影师叫伊藤秀夫,他想着拍点显摆日军威风的照片,就找到了南京一家叫吉祥照相馆的。**没想到,这些老百姓因为洗照片,反而躲过一劫。照片洗出来伊藤秀夫慢慢发现,日军那些干的事儿可一点都不威风。杀人、强奸、抢东西,这些血腥场面电影里都*直白地***,看得人心里直发毛。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这种手,那罪可就大了去了。可战后要给这些罪责定个谱,事情还真不那么容易办。电影里说了,战后有些日军内部就搞这套,说他们是忠于天皇,把杀人这些事儿说得好**为民除害一样。到了战后法庭上,那些战犯还死不认账,说要不是中国军队早跑了,南京老百姓哪会遭罪?要不是南京几位市民留了那些照片作证,这些日本战犯指不定就真脱罪了呢?要说这追查正义的事儿,不光是亚洲,欧洲那边对纳粹的审判,也是一场*漫长的“搞正义”的社会实验。这场实验持续了小几十年,全为啥追查正义会这么难。谁是受害者?谁该受罚?什么样的罚才算合适?这些问题都*模糊,没有标准答案。玛丽·弗尔布鲁克写的《大清算》里就说了,这场审判*费劲的,*暧昧的,破除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审判里,“正义”**概念会变的,不同国家、对不同人,正义就不一样。有些罪大恶极的,反而被轻易放过了;有些人又***远超他们过错的惩罚。这场本想搞“正义”的审判,最后反而成了政治、利益拉扯的复杂游戏。1963年到1965年,法兰克福开了个审奥斯维辛的庭,这庭在德国人眼里,算是他们“面对历史”的一个标志。这主要是因为奥斯维辛太重要了,审判过程中揭的罪行也太吓人了。审判发起者的目标也*明确的,就是要整个大规模灭绝的系统上法庭,不光是审几个个体。在媒体上***凶,大家看法也两极分化。在非犹太学者和普通读者里,纳粹大屠杀的地位算是确立了。可要说司法清算上,奥斯维辛这审判反倒说明了,这种事儿想办成,太难了。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豆瓣上打出了8.6分,今年夏天算是个爆款了。故事是这么回事,当年日军有个随军摄影师叫伊藤秀夫,他想着拍点显摆日军威风的照片,就找到了南京一家叫吉祥照相馆的。**没想到,这些老百姓因为洗照片,反而躲过一劫。照片洗出来伊藤秀夫慢慢发现,日军那些干的事儿可一点都不威风。杀人、强奸、抢东西,这些血腥场面电影里都*直白地***,看得人心里直发毛。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这种手,那罪可就大了去了。可战后要给这些罪责定个谱,事情还真不那么容易办。电影里说了,战后有些日军内部就搞这套,说他们是忠于天皇,把杀人这些事儿说得好**为民除害一样。到了战后法庭上,那些战犯还死不认账,说要不是中国军队早跑了,南京老百姓哪会遭罪?要不是南京几位市民留了那些照片作证,这些日本战犯指不定就真脱罪了呢?要说这追查正义的事儿,不光是亚洲,欧洲那边对纳粹的审判,也是一场*漫长的“搞正义”的社会实验。这场实验持续了小几十年,全为啥追查正义会这么难。谁是受害者?谁该受罚?什么样的罚才算合适?这些问题都*模糊,没有标准答案。玛丽·弗尔布鲁克写的《大清算》里就说了,这场审判*费劲的,*暧昧的,破除了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审判里,“正义”**概念会变的,不同国家、对不同人,正义就不一样。有些罪大恶极的,反而被轻易放过了;有些人又***远超他们过错的惩罚。这场本想搞“正义”的审判,最后反而成了政治、利益拉扯的复杂游戏。1963年到1965年,法兰克福开了个审奥斯维辛的庭,这庭在德国人眼里,算是他们“面对历史”的一个标志。这主要是因为奥斯维辛太重要了,审判过程中揭的罪行也太吓人了。审判发起者的目标也*明确的,就是要整个大规模灭绝的系统上法庭,不光是审几个个体。在媒体上***凶,大家看法也两极分化。在非犹太学者和普通读者里,纳粹大屠杀的地位算是确立了。可要说司法清算上,奥斯维辛这审判反倒说明了,这种事儿想办成,太难了。 要往法庭上对一个大规模杀人的系统下判决,几乎不**。一个国家发动、支持这种集体暴力,还让普通人跟着掺和进来,要用个体罪责去审,那**难上加难。《纽伦堡:纳粹战犯在审判》里就说了,奥斯维辛那会儿,光党卫队队员就有八千多名,女性守卫也有两百多个,这些人在西德受审的没几人,剩下的大多没上过法庭。法兰克福这审奥斯维辛的庭,检察官挑被告的时候也*费劲的,得选那些他们觉得最能定罪的人。不光要考虑被告在集中营系统里干啥,还得挑那些容易被揪出来,又能显出凶手的残忍和虐待的。这些被告在德国叫“作案人”(Täter),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干这些事儿没动过脑子,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么说跟事儿没多大关系,对实际发生的事儿不太清楚,不负责杀人的事儿,就是听命令,不听命令就得遭殃。审判里,有些证人遭的罪也不小,尤其有个叫汉斯·拉特恩泽尔的辩护律师,手段*狠的。他经常拿证人记不清日期啊什么的开玩笑,暗示证人是在撒谎。辩护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把被告说成是“希特勒的受害者”。1965年8月20日,审判长汉斯·霍夫迈耶(HansHofmeyer)念完判决书,这审就结束了。***德国已经不用死刑了,所以判决里*没人判死刑。在20个被告里,只有6人判了终身监禁,10个人判了3.5年到14年的刑,有个小时候就参与进来的,按未成年人的规矩判,还有3个因为证据不够,判了无罪。审判快结束时,西比尔·贝德福德说,**法官霍夫迈耶博士,平时*稳的,能让法庭保持冷静,可审完之后,他自己却崩溃了。要是单看把干坏事的人绳之以法,这***失望的。按罪行看,好多判决都*轻的,再说,要运转奥斯维辛,光是要6000到8000人,实际被判的才17人。鲍尔确实把奥斯维辛给闹大了,可离他想的正义差得远。在这过程中,他也觉得,反对他的人*多,离开办公室都觉得自己像在“敌人的地盘上”。赔偿,那也是另一回事了。受害者想拿点补偿,**被拒,或者给的数目太小,觉得*没劲的。可那些当年跟着希特勒干活的公务员、法官、医生啥的,战后继续干,还能拿高工资、拿全额退休金。这种事儿一出来,不公正的感觉就*。
要往法庭上对一个大规模杀人的系统下判决,几乎不**。一个国家发动、支持这种集体暴力,还让普通人跟着掺和进来,要用个体罪责去审,那**难上加难。《纽伦堡:纳粹战犯在审判》里就说了,奥斯维辛那会儿,光党卫队队员就有八千多名,女性守卫也有两百多个,这些人在西德受审的没几人,剩下的大多没上过法庭。法兰克福这审奥斯维辛的庭,检察官挑被告的时候也*费劲的,得选那些他们觉得最能定罪的人。不光要考虑被告在集中营系统里干啥,还得挑那些容易被揪出来,又能显出凶手的残忍和虐待的。这些被告在德国叫“作案人”(Täter),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干这些事儿没动过脑子,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么说跟事儿没多大关系,对实际发生的事儿不太清楚,不负责杀人的事儿,就是听命令,不听命令就得遭殃。审判里,有些证人遭的罪也不小,尤其有个叫汉斯·拉特恩泽尔的辩护律师,手段*狠的。他经常拿证人记不清日期啊什么的开玩笑,暗示证人是在撒谎。辩护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把被告说成是“希特勒的受害者”。1965年8月20日,审判长汉斯·霍夫迈耶(HansHofmeyer)念完判决书,这审就结束了。***德国已经不用死刑了,所以判决里*没人判死刑。在20个被告里,只有6人判了终身监禁,10个人判了3.5年到14年的刑,有个小时候就参与进来的,按未成年人的规矩判,还有3个因为证据不够,判了无罪。审判快结束时,西比尔·贝德福德说,**法官霍夫迈耶博士,平时*稳的,能让法庭保持冷静,可审完之后,他自己却崩溃了。要是单看把干坏事的人绳之以法,这***失望的。按罪行看,好多判决都*轻的,再说,要运转奥斯维辛,光是要6000到8000人,实际被判的才17人。鲍尔确实把奥斯维辛给闹大了,可离他想的正义差得远。在这过程中,他也觉得,反对他的人*多,离开办公室都觉得自己像在“敌人的地盘上”。赔偿,那也是另一回事了。受害者想拿点补偿,**被拒,或者给的数目太小,觉得*没劲的。可那些当年跟着希特勒干活的公务员、法官、医生啥的,战后继续干,还能拿高工资、拿全额退休金。这种事儿一出来,不公正的感觉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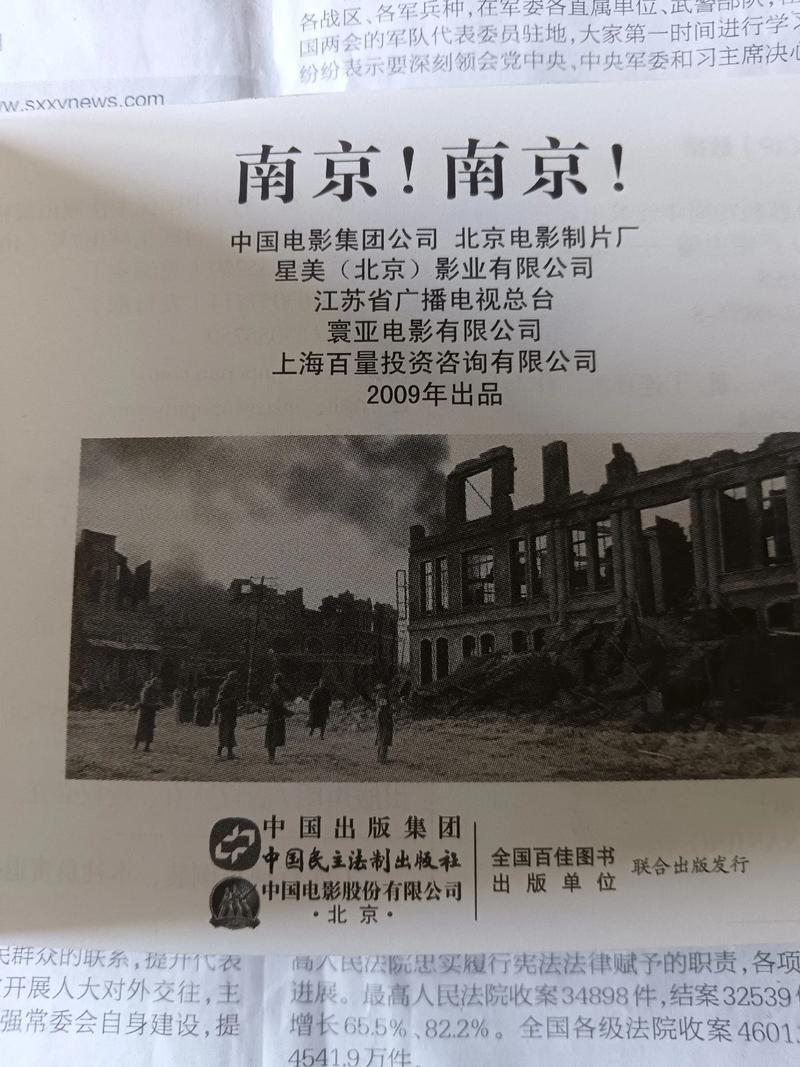 毫无疑问,啥措施也弥补不了纳粹的罪过,也救不回那些死的人。幸存者要的赔偿,跟他们受的苦比起来,确实差远了,可要拿到这笔钱,也难。那些管发补偿的人,跟以前政府关系**还*好。还存在其他不公平,**有些幸存者组织得厉害,有些群体就被忽视了,**还有偏见啥的,政治环境、舆论风向也影响事儿。在第三帝国的继承国里,没哪个国家给所有受害者全补偿。民主德国把国家社会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不愿意承认自己欠补偿。苏联主要想拿点钱来重建,从东德弄了不少东西。奥地利也不愿意给,想搞个“奥地利”民族身份,不想想起以前的事。后继政府和老百姓都*不想承认自己得补偿受害者的。因为纳粹的“罪”在法律上被说成是集中营守卫的虐待,所以能要求赔偿的受害者就少了。汉斯·弗兰肯塔尔说,他和弟弟在I.G.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当奴隶劳工,总共只拿到了1万马克,补偿工厂把他们当奴隶,补偿当局把他们遣送,补偿他们失去的青春、在集中营的遭遇、亲人没了,还有一辈子身体心理问题。有些群体的歧视没断,**“反社会人士”或“罪犯”那些人。反吉卜赛政策在战后德国还实行着,好多官员当年就“处理”过罗姆人和辛提人,还是那套看法。用这点钱来摆脱责任,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就是靠**。在50年代,德国政府站在道德高地上,那些大罪没受到实际惩罚,反而躲在个“责任”的幌子后面。给剩下的幸存者这点钱,是巩固了德国能面对过去的名声,但*没真解决罪责问题。**进步是有的,但即便是参与要赔偿、建立“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的人,也承认这迟来的正义不完整。痛苦、磨难和不公正的档案、证言、口供,好像永远也翻不完。那些司法调查、幸存者的痛苦证言,对司法正义没啥用了,只能当历史资料。若干坏事的人基本上都逃了惩罚,那只有无辜的人会继续受苦。就算他们等到上法庭那天,那也**不是个好地方。清算过去是个大故事,审判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家更多精力用在家人朋友邻里之间的瓜,或者自己写回忆录啥的,比法庭上的对抗还多。私下清算不像法庭判决那么清楚,是个没明确目标、总变来变去的过程。“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得改改了。深度追踪对施暴者的审判和反思,看“制度之恶”怎么操控“弱点”达成集体暴力。在伤痛慢慢淡了得再听听幸存者的声音。
毫无疑问,啥措施也弥补不了纳粹的罪过,也救不回那些死的人。幸存者要的赔偿,跟他们受的苦比起来,确实差远了,可要拿到这笔钱,也难。那些管发补偿的人,跟以前政府关系**还*好。还存在其他不公平,**有些幸存者组织得厉害,有些群体就被忽视了,**还有偏见啥的,政治环境、舆论风向也影响事儿。在第三帝国的继承国里,没哪个国家给所有受害者全补偿。民主德国把国家社会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不愿意承认自己欠补偿。苏联主要想拿点钱来重建,从东德弄了不少东西。奥地利也不愿意给,想搞个“奥地利”民族身份,不想想起以前的事。后继政府和老百姓都*不想承认自己得补偿受害者的。因为纳粹的“罪”在法律上被说成是集中营守卫的虐待,所以能要求赔偿的受害者就少了。汉斯·弗兰肯塔尔说,他和弟弟在I.G.法尔本丁钠橡胶工厂当奴隶劳工,总共只拿到了1万马克,补偿工厂把他们当奴隶,补偿当局把他们遣送,补偿他们失去的青春、在集中营的遭遇、亲人没了,还有一辈子身体心理问题。有些群体的歧视没断,**“反社会人士”或“罪犯”那些人。反吉卜赛政策在战后德国还实行着,好多官员当年就“处理”过罗姆人和辛提人,还是那套看法。用这点钱来摆脱责任,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就是靠**。在50年代,德国政府站在道德高地上,那些大罪没受到实际惩罚,反而躲在个“责任”的幌子后面。给剩下的幸存者这点钱,是巩固了德国能面对过去的名声,但*没真解决罪责问题。**进步是有的,但即便是参与要赔偿、建立“铭记、责任和未来”基金会的人,也承认这迟来的正义不完整。痛苦、磨难和不公正的档案、证言、口供,好像永远也翻不完。那些司法调查、幸存者的痛苦证言,对司法正义没啥用了,只能当历史资料。若干坏事的人基本上都逃了惩罚,那只有无辜的人会继续受苦。就算他们等到上法庭那天,那也**不是个好地方。清算过去是个大故事,审判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家更多精力用在家人朋友邻里之间的瓜,或者自己写回忆录啥的,比法庭上的对抗还多。私下清算不像法庭判决那么清楚,是个没明确目标、总变来变去的过程。“二战”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的说法,得改改了。深度追踪对施暴者的审判和反思,看“制度之恶”怎么操控“弱点”达成集体暴力。在伤痛慢慢淡了得再听听幸存者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