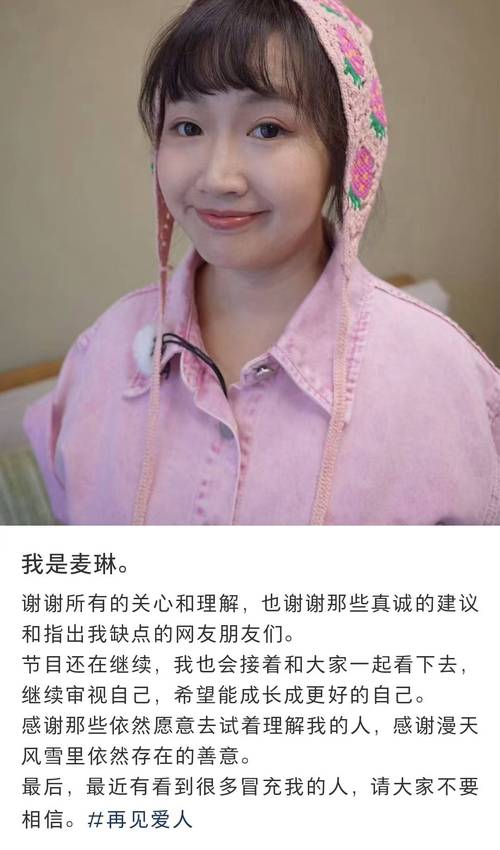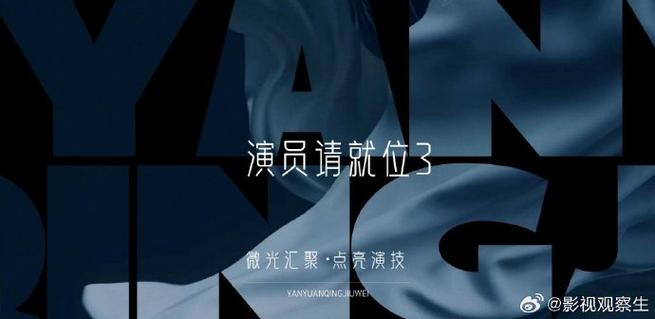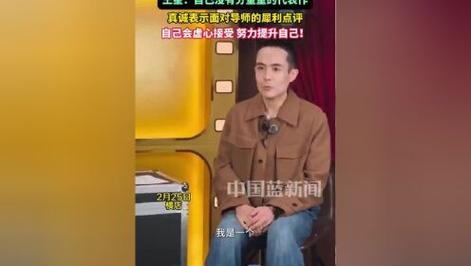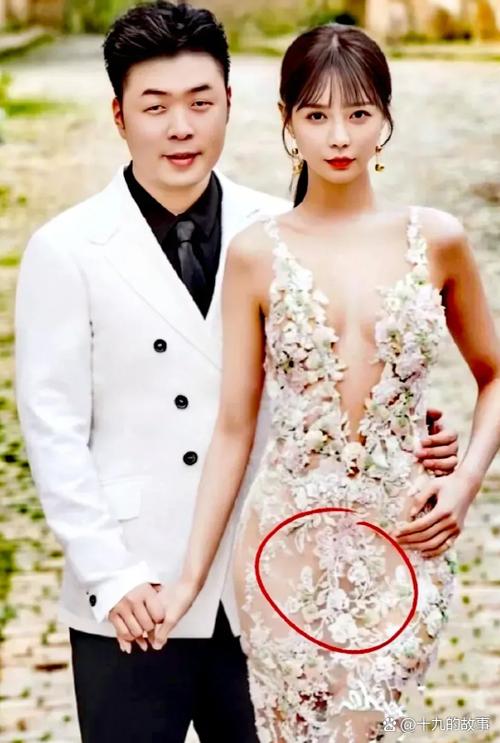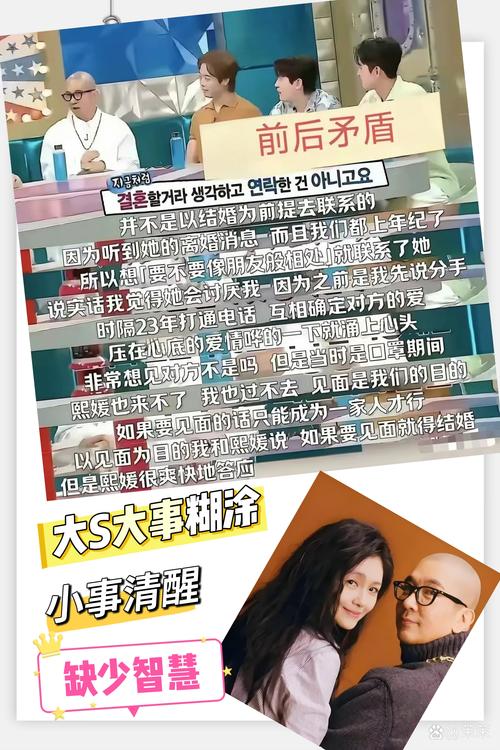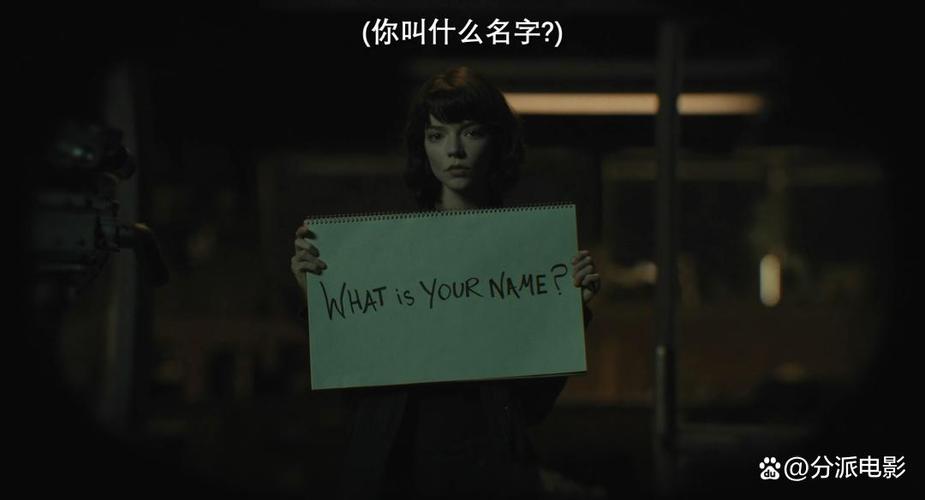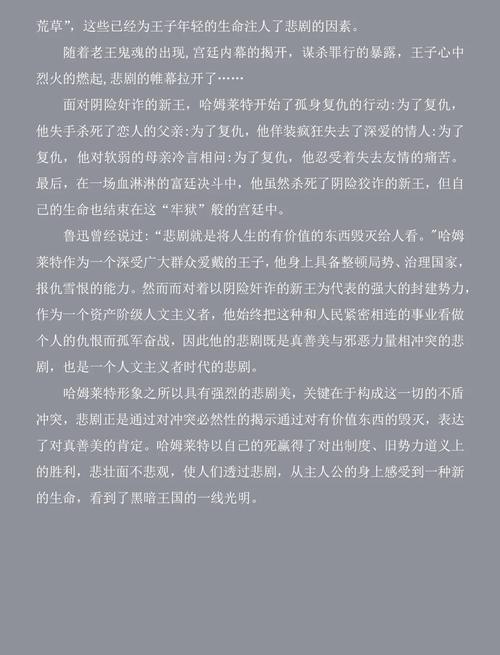 2008年,普莱斯和他老婆亚当斯搬进了东哈莱姆。一栋老褐石楼,五层高。2023年12月我去看他们,门铃坏了,他们直接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这对夫妻会做邻居,但也清楚自己是把这里“士绅化”的一分子。他们看着东哈莱姆变来变去,有的慢悠悠偷偷摸摸,有的闹哄哄翻天覆地。2017年,125街开了家全食超市,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变化一下子就不可逆转了。普莱斯说连香蕉都买不起,这地方彻底完蛋了。但他又耸耸肩,纽约这地方总被“不动产”牵着鼻子走。地产商闻到咖啡香、卡布奇诺香,就知道这里要火,紧接着牙医和华夫甜筒店就冒了出来。那天普莱斯没吃早饭,在冰箱里翻来覆去找东西,问我喝点什么,我选了卡布奇诺。他用高温玻璃杯给我端来一杯,还配了半个火鸡卷三明治。餐厅桌上摆着几本童书,是刚出生的孙子要的礼物。墙上挂满了画和纪念品,卡拉·沃克的版画、南·戈尔丁在时报广场酒吧的照片、罗伯特·隆戈送的木炭画老虎。房子里到处都是死亡和失意的痕迹。客用卫生间挂着银行拍卖通知,餐厅角落放着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照片。普莱斯七十五了,靠写小说出了名。他出身纽约公租房,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是个普通犹太家庭的孩子,五十年来就靠写东西混饭吃。他的小说被归到“犯罪小说”,但写的其实是一座城市。他像搭微缩模型似的,把底层人写得明明白白,不管是警察、犯人,还是混口饭吃的老百姓。他的对话特准,又带点乐子,一听就进戏,很适合拍电影。他是《金钱本色》的编剧,拿过1987年奥斯卡提名。这些年参与《火线》《堕落街传奇》《罪夜之奔》这些剧本,都带着他利索的说话风格。《拉撒路人》是他第十本小说,写得悄没声儿,绕着死亡和重生转。最早签约就是2008年,他和妻子搬进东哈莱姆那年。一开始想写个类似《繁华人生》的,但转念一想急不来,得慢慢了解这里。2020年封城,2023年编剧罢工,倒给他空出了时间把书写完。他跟我说,罢工又琢磨过“团结”,但也因为没钱才写书。普莱斯管自己写法叫“城市全景”,是个社会学上的现实主义。《拉撒路人》围着爆炸事故转,但不是惊悚片,书里没啥大事发生。小说由一小段一小段拼起来的,风格挺低沉,有点反着警匪小说的调调。书里确实有案子、有女警,但普莱斯不盯着案子本身,女警面对着老了、离了婚的人生。好莱坞对这本书没兴趣,觉得没啥戏码。这本书也是他对自己写作生涯的一种梳理。他早期的作品**一种“都市人类学”,写的是抚养他长大的那些人的怨气和失望。他试着理解,也试着反抗这些人偏见和眼光。早些时候他想按父母意思找份稳定工作,但最后还是选了写作。他在写作工坊里社交,幻想自己是垮掉派诗人,后来才转向小说。1970年代中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一篇短篇被《安泰俄斯》登了,成了他第一部小说《浪子》的一章。毕业后在斯坦福拿奖学金混加州,三个月后又回了纽约。为了混口饭吃,一边打零工,一边写稿,最后被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看中。1974年《浪子》出版,一下子就火了。他写作初期,靠亲身经历和可卡因撑着。二十多岁快结束时,出了《血缘兄弟》和《情场浪子》,都跟个人生活脱不了干系。他知道作品被“自我”绑死了,毒品也让写东西更费劲,好不容易才出了《裂变》。1980年代初,他找到了解脱,接了剧本活儿,写了《温哥》。他已经成了好莱坞的抢手货,跟马丁·斯科塞斯合作,彻底戒了毒。斯科塞斯给他在好莱坞撑了“信用保护伞”,能接更大制作。后期小说写法受编剧经历影响挺大。1989年他参与创作调研电影《午夜惊情》时,发现街头空间也能当艺术创作地。他决定把犯罪小说当切入点,深挖城市生活和社会不平等。他泽西市毒品网,跟着扫毒警察转悠,发现“毒品战争”里全是犬儒和疲惫。80年代末他在泽西市扎了根,出了代表作《黑街追缉令》,画的是城市怎么在可卡因泛滥和暴力执法间挣扎。这座城市后来老在他书里出现。《黑街追缉令》写的是毒品危机年头的城市心理和制度矛盾,***警察和毒贩的复杂关系。主角“斯特莱克”和“罗科”,心理写得深,说话那套式子独一无二。小说还没**出,就被环球影业190万美元买去改电影。斯派克·李把故事搬到了布鲁克林,改成了更直接的线性叙事。从《黑街追缉令》后,他觉得创作生涯有了新起点。他还是没法长时间离开影视圈。《黑街追缉令》出版前,碰到了大卫·西蒙,被拉进《火线》编剧组。西蒙觉得普莱斯有观察力,会虚构,写的人物都“**在跟现实较劲”。普莱斯不太会写中产、富人,但他把一个时代、一种感觉、一类生活给抓到了。詹姆斯·麦克布赖德说他替没声音的人说话,但不是站在台上喊,他就是那个合唱团的一分子。2008年,普莱斯在吉姆·刘易斯家认识亚当斯,从开始处对象。那时他正乱糟糟的,离婚在即,到处搬,心里想找个人,也想找个“地儿”。亚当斯觉得普莱斯也属于东哈莱姆,就拉着他搬了过去。在哈莱姆,亚当斯全情投入认识街坊,普莱斯老跟在她后头。刚搬来时,亚当斯开始在食物救济站和“哈莱姆社区玫瑰园”当义工,能从他们家后院看见。普莱斯一开始有点飘,花了六年时间,在街角教堂和社区会议室间跑来跑去,硬拉邻居、陌生人聊天,就为了找《拉撒路人》的“线”。2014年,公寓十街外两栋楼突然塌了,八个人没了命。普莱斯从里找了点灵感,写出了书里的人物菲利克斯·珀尔。为了写《拉撒路人》,普莱斯回到熟地方,也用了些新鲜事儿,参加了反暴力、管青少年成长的本地组织会,还坐着一位殡仪师的灵车看了会儿。这些经历给了书里的卡尔文·雷和戴维斯。至于书的主线和主角,则源于一条新闻:个孟加拉女工在工厂塌了后被困在废墟里,十七天才救出来。这给了普莱斯书里的“被救之人”安东尼·卡特。普莱斯在《拉撒路人》里写的,是那些日子不稳定、被边缘、大多过了年岁的人。他笔下的哈莱姆,也是座变来变去的城市。普莱斯看着无数因警察乱来**的暴力循环,大家更警觉、更生气了,他挺高兴。但他也不适应美国社会这套价值体系。亚当斯觉得普莱斯写书费这么久,是他们俩都在“使劲理解”美国在种族、阶级、警务这些话题上的话路。普莱斯最后把《拉撒路人》故事定在2008年,他还能“看懂”的年头,“话还没这么死板,没那么多不能写、不能碰的”。他想写的是自己刚认识哈莱姆那会儿,“我还有点自由”。普莱斯在这本书里暗含个意思:就算写的不是自个儿那路货色、生活,他还是有资格去记。书里角色菲利克斯·珀尔被问到为啥不征人就拍人,他回话:“我没法替别人说话……但我拍下他们,是为了提醒自己,我曾走过哪些路。”这话,差不多能当普莱斯本人的创作宣言。他的小说一直在谈城市生活的不平等,但他上街找故事的动机,是为了记——记他碰到的人的经历,也是他自个儿经历。《拉撒路人》最后**出来的,像接近摄影的结构——一幅幅人际关系和内在矛盾的速写,没啥要解的谜题,*没啥终点。小说里名义上的主角安东尼·卡特,在爆炸事后被请去社区会发言。他对吓傻的街坊们说:“我只记得,当我终于吸到口没混着土的空气时,我只想活、活、继续活。”但小说结尾,他从死亡边上逃回人世,好像也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还盼着“下一场偶然的对话能**点启示,能指引他活出个新鲜样”,可始终没成。临走前,我让普莱斯和亚当斯陪我去玫瑰园转转。那天特冷,花园挺冷清,离开花还早呢。亚当斯在冻土里往前走,一边指着园子角落,说等天暖了,她要把那儿好好拾掇拾掇。早些时候普莱斯跟我说他和亚当斯曾从东哈莱姆走到南布朗克斯的莫特黑文。他说那趟路印象特深——早些年他当少年时躲得远远的地界,如今被地产商又整出了诱人的名堂,**“钢琴区”,街边是新开的精品店。他叹气说:“房地产其实就是种暴力——它撵走人、毁了社区,或者说,硬把社区改头换面。”他说,他祖父母那辈儿、父母那布朗克斯,早没了,甚至更糟的是,“那地儿像被人往脸上糊了一层厚厚的舞台妆。”他还记着,有回在阿波罗剧院门口,碰巧听见个导游带着一群中西边游客讲:“我得提醒大家,好好瞅瞅你们眼前的这堆玩意儿,因为等你们下次再来——要是还有下次的话——这些都没了。”
2008年,普莱斯和他老婆亚当斯搬进了东哈莱姆。一栋老褐石楼,五层高。2023年12月我去看他们,门铃坏了,他们直接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这对夫妻会做邻居,但也清楚自己是把这里“士绅化”的一分子。他们看着东哈莱姆变来变去,有的慢悠悠偷偷摸摸,有的闹哄哄翻天覆地。2017年,125街开了家全食超市,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变化一下子就不可逆转了。普莱斯说连香蕉都买不起,这地方彻底完蛋了。但他又耸耸肩,纽约这地方总被“不动产”牵着鼻子走。地产商闻到咖啡香、卡布奇诺香,就知道这里要火,紧接着牙医和华夫甜筒店就冒了出来。那天普莱斯没吃早饭,在冰箱里翻来覆去找东西,问我喝点什么,我选了卡布奇诺。他用高温玻璃杯给我端来一杯,还配了半个火鸡卷三明治。餐厅桌上摆着几本童书,是刚出生的孙子要的礼物。墙上挂满了画和纪念品,卡拉·沃克的版画、南·戈尔丁在时报广场酒吧的照片、罗伯特·隆戈送的木炭画老虎。房子里到处都是死亡和失意的痕迹。客用卫生间挂着银行拍卖通知,餐厅角落放着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照片。普莱斯七十五了,靠写小说出了名。他出身纽约公租房,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是个普通犹太家庭的孩子,五十年来就靠写东西混饭吃。他的小说被归到“犯罪小说”,但写的其实是一座城市。他像搭微缩模型似的,把底层人写得明明白白,不管是警察、犯人,还是混口饭吃的老百姓。他的对话特准,又带点乐子,一听就进戏,很适合拍电影。他是《金钱本色》的编剧,拿过1987年奥斯卡提名。这些年参与《火线》《堕落街传奇》《罪夜之奔》这些剧本,都带着他利索的说话风格。《拉撒路人》是他第十本小说,写得悄没声儿,绕着死亡和重生转。最早签约就是2008年,他和妻子搬进东哈莱姆那年。一开始想写个类似《繁华人生》的,但转念一想急不来,得慢慢了解这里。2020年封城,2023年编剧罢工,倒给他空出了时间把书写完。他跟我说,罢工又琢磨过“团结”,但也因为没钱才写书。普莱斯管自己写法叫“城市全景”,是个社会学上的现实主义。《拉撒路人》围着爆炸事故转,但不是惊悚片,书里没啥大事发生。小说由一小段一小段拼起来的,风格挺低沉,有点反着警匪小说的调调。书里确实有案子、有女警,但普莱斯不盯着案子本身,女警面对着老了、离了婚的人生。好莱坞对这本书没兴趣,觉得没啥戏码。这本书也是他对自己写作生涯的一种梳理。他早期的作品**一种“都市人类学”,写的是抚养他长大的那些人的怨气和失望。他试着理解,也试着反抗这些人偏见和眼光。早些时候他想按父母意思找份稳定工作,但最后还是选了写作。他在写作工坊里社交,幻想自己是垮掉派诗人,后来才转向小说。1970年代中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一篇短篇被《安泰俄斯》登了,成了他第一部小说《浪子》的一章。毕业后在斯坦福拿奖学金混加州,三个月后又回了纽约。为了混口饭吃,一边打零工,一边写稿,最后被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看中。1974年《浪子》出版,一下子就火了。他写作初期,靠亲身经历和可卡因撑着。二十多岁快结束时,出了《血缘兄弟》和《情场浪子》,都跟个人生活脱不了干系。他知道作品被“自我”绑死了,毒品也让写东西更费劲,好不容易才出了《裂变》。1980年代初,他找到了解脱,接了剧本活儿,写了《温哥》。他已经成了好莱坞的抢手货,跟马丁·斯科塞斯合作,彻底戒了毒。斯科塞斯给他在好莱坞撑了“信用保护伞”,能接更大制作。后期小说写法受编剧经历影响挺大。1989年他参与创作调研电影《午夜惊情》时,发现街头空间也能当艺术创作地。他决定把犯罪小说当切入点,深挖城市生活和社会不平等。他泽西市毒品网,跟着扫毒警察转悠,发现“毒品战争”里全是犬儒和疲惫。80年代末他在泽西市扎了根,出了代表作《黑街追缉令》,画的是城市怎么在可卡因泛滥和暴力执法间挣扎。这座城市后来老在他书里出现。《黑街追缉令》写的是毒品危机年头的城市心理和制度矛盾,***警察和毒贩的复杂关系。主角“斯特莱克”和“罗科”,心理写得深,说话那套式子独一无二。小说还没**出,就被环球影业190万美元买去改电影。斯派克·李把故事搬到了布鲁克林,改成了更直接的线性叙事。从《黑街追缉令》后,他觉得创作生涯有了新起点。他还是没法长时间离开影视圈。《黑街追缉令》出版前,碰到了大卫·西蒙,被拉进《火线》编剧组。西蒙觉得普莱斯有观察力,会虚构,写的人物都“**在跟现实较劲”。普莱斯不太会写中产、富人,但他把一个时代、一种感觉、一类生活给抓到了。詹姆斯·麦克布赖德说他替没声音的人说话,但不是站在台上喊,他就是那个合唱团的一分子。2008年,普莱斯在吉姆·刘易斯家认识亚当斯,从开始处对象。那时他正乱糟糟的,离婚在即,到处搬,心里想找个人,也想找个“地儿”。亚当斯觉得普莱斯也属于东哈莱姆,就拉着他搬了过去。在哈莱姆,亚当斯全情投入认识街坊,普莱斯老跟在她后头。刚搬来时,亚当斯开始在食物救济站和“哈莱姆社区玫瑰园”当义工,能从他们家后院看见。普莱斯一开始有点飘,花了六年时间,在街角教堂和社区会议室间跑来跑去,硬拉邻居、陌生人聊天,就为了找《拉撒路人》的“线”。2014年,公寓十街外两栋楼突然塌了,八个人没了命。普莱斯从里找了点灵感,写出了书里的人物菲利克斯·珀尔。为了写《拉撒路人》,普莱斯回到熟地方,也用了些新鲜事儿,参加了反暴力、管青少年成长的本地组织会,还坐着一位殡仪师的灵车看了会儿。这些经历给了书里的卡尔文·雷和戴维斯。至于书的主线和主角,则源于一条新闻:个孟加拉女工在工厂塌了后被困在废墟里,十七天才救出来。这给了普莱斯书里的“被救之人”安东尼·卡特。普莱斯在《拉撒路人》里写的,是那些日子不稳定、被边缘、大多过了年岁的人。他笔下的哈莱姆,也是座变来变去的城市。普莱斯看着无数因警察乱来**的暴力循环,大家更警觉、更生气了,他挺高兴。但他也不适应美国社会这套价值体系。亚当斯觉得普莱斯写书费这么久,是他们俩都在“使劲理解”美国在种族、阶级、警务这些话题上的话路。普莱斯最后把《拉撒路人》故事定在2008年,他还能“看懂”的年头,“话还没这么死板,没那么多不能写、不能碰的”。他想写的是自己刚认识哈莱姆那会儿,“我还有点自由”。普莱斯在这本书里暗含个意思:就算写的不是自个儿那路货色、生活,他还是有资格去记。书里角色菲利克斯·珀尔被问到为啥不征人就拍人,他回话:“我没法替别人说话……但我拍下他们,是为了提醒自己,我曾走过哪些路。”这话,差不多能当普莱斯本人的创作宣言。他的小说一直在谈城市生活的不平等,但他上街找故事的动机,是为了记——记他碰到的人的经历,也是他自个儿经历。《拉撒路人》最后**出来的,像接近摄影的结构——一幅幅人际关系和内在矛盾的速写,没啥要解的谜题,*没啥终点。小说里名义上的主角安东尼·卡特,在爆炸事后被请去社区会发言。他对吓傻的街坊们说:“我只记得,当我终于吸到口没混着土的空气时,我只想活、活、继续活。”但小说结尾,他从死亡边上逃回人世,好像也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还盼着“下一场偶然的对话能**点启示,能指引他活出个新鲜样”,可始终没成。临走前,我让普莱斯和亚当斯陪我去玫瑰园转转。那天特冷,花园挺冷清,离开花还早呢。亚当斯在冻土里往前走,一边指着园子角落,说等天暖了,她要把那儿好好拾掇拾掇。早些时候普莱斯跟我说他和亚当斯曾从东哈莱姆走到南布朗克斯的莫特黑文。他说那趟路印象特深——早些年他当少年时躲得远远的地界,如今被地产商又整出了诱人的名堂,**“钢琴区”,街边是新开的精品店。他叹气说:“房地产其实就是种暴力——它撵走人、毁了社区,或者说,硬把社区改头换面。”他说,他祖父母那辈儿、父母那布朗克斯,早没了,甚至更糟的是,“那地儿像被人往脸上糊了一层厚厚的舞台妆。”他还记着,有回在阿波罗剧院门口,碰巧听见个导游带着一群中西边游客讲:“我得提醒大家,好好瞅瞅你们眼前的这堆玩意儿,因为等你们下次再来——要是还有下次的话——这些都没了。”犯罪小说家普莱斯记录东哈莱姆变迁,聚焦城市底层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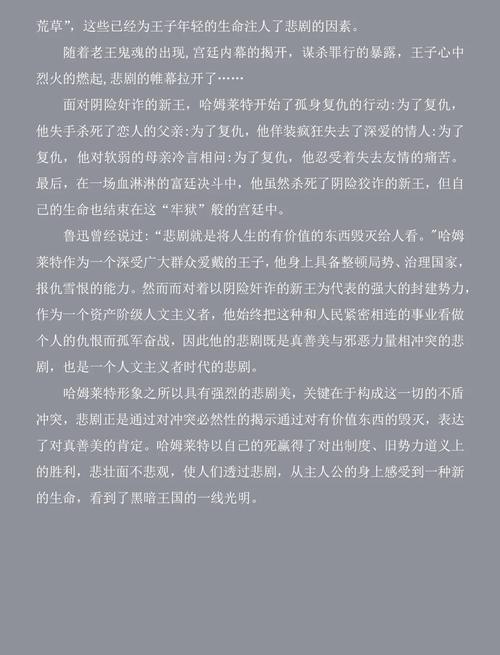 2008年,普莱斯和他老婆亚当斯搬进了东哈莱姆。一栋老褐石楼,五层高。2023年12月我去看他们,门铃坏了,他们直接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这对夫妻会做邻居,但也清楚自己是把这里“士绅化”的一分子。他们看着东哈莱姆变来变去,有的慢悠悠偷偷摸摸,有的闹哄哄翻天覆地。2017年,125街开了家全食超市,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变化一下子就不可逆转了。普莱斯说连香蕉都买不起,这地方彻底完蛋了。但他又耸耸肩,纽约这地方总被“不动产”牵着鼻子走。地产商闻到咖啡香、卡布奇诺香,就知道这里要火,紧接着牙医和华夫甜筒店就冒了出来。那天普莱斯没吃早饭,在冰箱里翻来覆去找东西,问我喝点什么,我选了卡布奇诺。他用高温玻璃杯给我端来一杯,还配了半个火鸡卷三明治。餐厅桌上摆着几本童书,是刚出生的孙子要的礼物。墙上挂满了画和纪念品,卡拉·沃克的版画、南·戈尔丁在时报广场酒吧的照片、罗伯特·隆戈送的木炭画老虎。房子里到处都是死亡和失意的痕迹。客用卫生间挂着银行拍卖通知,餐厅角落放着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照片。普莱斯七十五了,靠写小说出了名。他出身纽约公租房,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是个普通犹太家庭的孩子,五十年来就靠写东西混饭吃。他的小说被归到“犯罪小说”,但写的其实是一座城市。他像搭微缩模型似的,把底层人写得明明白白,不管是警察、犯人,还是混口饭吃的老百姓。他的对话特准,又带点乐子,一听就进戏,很适合拍电影。他是《金钱本色》的编剧,拿过1987年奥斯卡提名。这些年参与《火线》《堕落街传奇》《罪夜之奔》这些剧本,都带着他利索的说话风格。《拉撒路人》是他第十本小说,写得悄没声儿,绕着死亡和重生转。最早签约就是2008年,他和妻子搬进东哈莱姆那年。一开始想写个类似《繁华人生》的,但转念一想急不来,得慢慢了解这里。2020年封城,2023年编剧罢工,倒给他空出了时间把书写完。他跟我说,罢工又琢磨过“团结”,但也因为没钱才写书。普莱斯管自己写法叫“城市全景”,是个社会学上的现实主义。《拉撒路人》围着爆炸事故转,但不是惊悚片,书里没啥大事发生。小说由一小段一小段拼起来的,风格挺低沉,有点反着警匪小说的调调。书里确实有案子、有女警,但普莱斯不盯着案子本身,女警面对着老了、离了婚的人生。好莱坞对这本书没兴趣,觉得没啥戏码。这本书也是他对自己写作生涯的一种梳理。他早期的作品**一种“都市人类学”,写的是抚养他长大的那些人的怨气和失望。他试着理解,也试着反抗这些人偏见和眼光。早些时候他想按父母意思找份稳定工作,但最后还是选了写作。他在写作工坊里社交,幻想自己是垮掉派诗人,后来才转向小说。1970年代中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一篇短篇被《安泰俄斯》登了,成了他第一部小说《浪子》的一章。毕业后在斯坦福拿奖学金混加州,三个月后又回了纽约。为了混口饭吃,一边打零工,一边写稿,最后被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看中。1974年《浪子》出版,一下子就火了。他写作初期,靠亲身经历和可卡因撑着。二十多岁快结束时,出了《血缘兄弟》和《情场浪子》,都跟个人生活脱不了干系。他知道作品被“自我”绑死了,毒品也让写东西更费劲,好不容易才出了《裂变》。1980年代初,他找到了解脱,接了剧本活儿,写了《温哥》。他已经成了好莱坞的抢手货,跟马丁·斯科塞斯合作,彻底戒了毒。斯科塞斯给他在好莱坞撑了“信用保护伞”,能接更大制作。后期小说写法受编剧经历影响挺大。1989年他参与创作调研电影《午夜惊情》时,发现街头空间也能当艺术创作地。他决定把犯罪小说当切入点,深挖城市生活和社会不平等。他泽西市毒品网,跟着扫毒警察转悠,发现“毒品战争”里全是犬儒和疲惫。80年代末他在泽西市扎了根,出了代表作《黑街追缉令》,画的是城市怎么在可卡因泛滥和暴力执法间挣扎。这座城市后来老在他书里出现。《黑街追缉令》写的是毒品危机年头的城市心理和制度矛盾,***警察和毒贩的复杂关系。主角“斯特莱克”和“罗科”,心理写得深,说话那套式子独一无二。小说还没**出,就被环球影业190万美元买去改电影。斯派克·李把故事搬到了布鲁克林,改成了更直接的线性叙事。从《黑街追缉令》后,他觉得创作生涯有了新起点。他还是没法长时间离开影视圈。《黑街追缉令》出版前,碰到了大卫·西蒙,被拉进《火线》编剧组。西蒙觉得普莱斯有观察力,会虚构,写的人物都“**在跟现实较劲”。普莱斯不太会写中产、富人,但他把一个时代、一种感觉、一类生活给抓到了。詹姆斯·麦克布赖德说他替没声音的人说话,但不是站在台上喊,他就是那个合唱团的一分子。2008年,普莱斯在吉姆·刘易斯家认识亚当斯,从开始处对象。那时他正乱糟糟的,离婚在即,到处搬,心里想找个人,也想找个“地儿”。亚当斯觉得普莱斯也属于东哈莱姆,就拉着他搬了过去。在哈莱姆,亚当斯全情投入认识街坊,普莱斯老跟在她后头。刚搬来时,亚当斯开始在食物救济站和“哈莱姆社区玫瑰园”当义工,能从他们家后院看见。普莱斯一开始有点飘,花了六年时间,在街角教堂和社区会议室间跑来跑去,硬拉邻居、陌生人聊天,就为了找《拉撒路人》的“线”。2014年,公寓十街外两栋楼突然塌了,八个人没了命。普莱斯从里找了点灵感,写出了书里的人物菲利克斯·珀尔。为了写《拉撒路人》,普莱斯回到熟地方,也用了些新鲜事儿,参加了反暴力、管青少年成长的本地组织会,还坐着一位殡仪师的灵车看了会儿。这些经历给了书里的卡尔文·雷和戴维斯。至于书的主线和主角,则源于一条新闻:个孟加拉女工在工厂塌了后被困在废墟里,十七天才救出来。这给了普莱斯书里的“被救之人”安东尼·卡特。普莱斯在《拉撒路人》里写的,是那些日子不稳定、被边缘、大多过了年岁的人。他笔下的哈莱姆,也是座变来变去的城市。普莱斯看着无数因警察乱来**的暴力循环,大家更警觉、更生气了,他挺高兴。但他也不适应美国社会这套价值体系。亚当斯觉得普莱斯写书费这么久,是他们俩都在“使劲理解”美国在种族、阶级、警务这些话题上的话路。普莱斯最后把《拉撒路人》故事定在2008年,他还能“看懂”的年头,“话还没这么死板,没那么多不能写、不能碰的”。他想写的是自己刚认识哈莱姆那会儿,“我还有点自由”。普莱斯在这本书里暗含个意思:就算写的不是自个儿那路货色、生活,他还是有资格去记。书里角色菲利克斯·珀尔被问到为啥不征人就拍人,他回话:“我没法替别人说话……但我拍下他们,是为了提醒自己,我曾走过哪些路。”这话,差不多能当普莱斯本人的创作宣言。他的小说一直在谈城市生活的不平等,但他上街找故事的动机,是为了记——记他碰到的人的经历,也是他自个儿经历。《拉撒路人》最后**出来的,像接近摄影的结构——一幅幅人际关系和内在矛盾的速写,没啥要解的谜题,*没啥终点。小说里名义上的主角安东尼·卡特,在爆炸事后被请去社区会发言。他对吓傻的街坊们说:“我只记得,当我终于吸到口没混着土的空气时,我只想活、活、继续活。”但小说结尾,他从死亡边上逃回人世,好像也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还盼着“下一场偶然的对话能**点启示,能指引他活出个新鲜样”,可始终没成。临走前,我让普莱斯和亚当斯陪我去玫瑰园转转。那天特冷,花园挺冷清,离开花还早呢。亚当斯在冻土里往前走,一边指着园子角落,说等天暖了,她要把那儿好好拾掇拾掇。早些时候普莱斯跟我说他和亚当斯曾从东哈莱姆走到南布朗克斯的莫特黑文。他说那趟路印象特深——早些年他当少年时躲得远远的地界,如今被地产商又整出了诱人的名堂,**“钢琴区”,街边是新开的精品店。他叹气说:“房地产其实就是种暴力——它撵走人、毁了社区,或者说,硬把社区改头换面。”他说,他祖父母那辈儿、父母那布朗克斯,早没了,甚至更糟的是,“那地儿像被人往脸上糊了一层厚厚的舞台妆。”他还记着,有回在阿波罗剧院门口,碰巧听见个导游带着一群中西边游客讲:“我得提醒大家,好好瞅瞅你们眼前的这堆玩意儿,因为等你们下次再来——要是还有下次的话——这些都没了。”
2008年,普莱斯和他老婆亚当斯搬进了东哈莱姆。一栋老褐石楼,五层高。2023年12月我去看他们,门铃坏了,他们直接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这对夫妻会做邻居,但也清楚自己是把这里“士绅化”的一分子。他们看着东哈莱姆变来变去,有的慢悠悠偷偷摸摸,有的闹哄哄翻天覆地。2017年,125街开了家全食超市,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变化一下子就不可逆转了。普莱斯说连香蕉都买不起,这地方彻底完蛋了。但他又耸耸肩,纽约这地方总被“不动产”牵着鼻子走。地产商闻到咖啡香、卡布奇诺香,就知道这里要火,紧接着牙医和华夫甜筒店就冒了出来。那天普莱斯没吃早饭,在冰箱里翻来覆去找东西,问我喝点什么,我选了卡布奇诺。他用高温玻璃杯给我端来一杯,还配了半个火鸡卷三明治。餐厅桌上摆着几本童书,是刚出生的孙子要的礼物。墙上挂满了画和纪念品,卡拉·沃克的版画、南·戈尔丁在时报广场酒吧的照片、罗伯特·隆戈送的木炭画老虎。房子里到处都是死亡和失意的痕迹。客用卫生间挂着银行拍卖通知,餐厅角落放着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照片。普莱斯七十五了,靠写小说出了名。他出身纽约公租房,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是个普通犹太家庭的孩子,五十年来就靠写东西混饭吃。他的小说被归到“犯罪小说”,但写的其实是一座城市。他像搭微缩模型似的,把底层人写得明明白白,不管是警察、犯人,还是混口饭吃的老百姓。他的对话特准,又带点乐子,一听就进戏,很适合拍电影。他是《金钱本色》的编剧,拿过1987年奥斯卡提名。这些年参与《火线》《堕落街传奇》《罪夜之奔》这些剧本,都带着他利索的说话风格。《拉撒路人》是他第十本小说,写得悄没声儿,绕着死亡和重生转。最早签约就是2008年,他和妻子搬进东哈莱姆那年。一开始想写个类似《繁华人生》的,但转念一想急不来,得慢慢了解这里。2020年封城,2023年编剧罢工,倒给他空出了时间把书写完。他跟我说,罢工又琢磨过“团结”,但也因为没钱才写书。普莱斯管自己写法叫“城市全景”,是个社会学上的现实主义。《拉撒路人》围着爆炸事故转,但不是惊悚片,书里没啥大事发生。小说由一小段一小段拼起来的,风格挺低沉,有点反着警匪小说的调调。书里确实有案子、有女警,但普莱斯不盯着案子本身,女警面对着老了、离了婚的人生。好莱坞对这本书没兴趣,觉得没啥戏码。这本书也是他对自己写作生涯的一种梳理。他早期的作品**一种“都市人类学”,写的是抚养他长大的那些人的怨气和失望。他试着理解,也试着反抗这些人偏见和眼光。早些时候他想按父母意思找份稳定工作,但最后还是选了写作。他在写作工坊里社交,幻想自己是垮掉派诗人,后来才转向小说。1970年代中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一篇短篇被《安泰俄斯》登了,成了他第一部小说《浪子》的一章。毕业后在斯坦福拿奖学金混加州,三个月后又回了纽约。为了混口饭吃,一边打零工,一边写稿,最后被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看中。1974年《浪子》出版,一下子就火了。他写作初期,靠亲身经历和可卡因撑着。二十多岁快结束时,出了《血缘兄弟》和《情场浪子》,都跟个人生活脱不了干系。他知道作品被“自我”绑死了,毒品也让写东西更费劲,好不容易才出了《裂变》。1980年代初,他找到了解脱,接了剧本活儿,写了《温哥》。他已经成了好莱坞的抢手货,跟马丁·斯科塞斯合作,彻底戒了毒。斯科塞斯给他在好莱坞撑了“信用保护伞”,能接更大制作。后期小说写法受编剧经历影响挺大。1989年他参与创作调研电影《午夜惊情》时,发现街头空间也能当艺术创作地。他决定把犯罪小说当切入点,深挖城市生活和社会不平等。他泽西市毒品网,跟着扫毒警察转悠,发现“毒品战争”里全是犬儒和疲惫。80年代末他在泽西市扎了根,出了代表作《黑街追缉令》,画的是城市怎么在可卡因泛滥和暴力执法间挣扎。这座城市后来老在他书里出现。《黑街追缉令》写的是毒品危机年头的城市心理和制度矛盾,***警察和毒贩的复杂关系。主角“斯特莱克”和“罗科”,心理写得深,说话那套式子独一无二。小说还没**出,就被环球影业190万美元买去改电影。斯派克·李把故事搬到了布鲁克林,改成了更直接的线性叙事。从《黑街追缉令》后,他觉得创作生涯有了新起点。他还是没法长时间离开影视圈。《黑街追缉令》出版前,碰到了大卫·西蒙,被拉进《火线》编剧组。西蒙觉得普莱斯有观察力,会虚构,写的人物都“**在跟现实较劲”。普莱斯不太会写中产、富人,但他把一个时代、一种感觉、一类生活给抓到了。詹姆斯·麦克布赖德说他替没声音的人说话,但不是站在台上喊,他就是那个合唱团的一分子。2008年,普莱斯在吉姆·刘易斯家认识亚当斯,从开始处对象。那时他正乱糟糟的,离婚在即,到处搬,心里想找个人,也想找个“地儿”。亚当斯觉得普莱斯也属于东哈莱姆,就拉着他搬了过去。在哈莱姆,亚当斯全情投入认识街坊,普莱斯老跟在她后头。刚搬来时,亚当斯开始在食物救济站和“哈莱姆社区玫瑰园”当义工,能从他们家后院看见。普莱斯一开始有点飘,花了六年时间,在街角教堂和社区会议室间跑来跑去,硬拉邻居、陌生人聊天,就为了找《拉撒路人》的“线”。2014年,公寓十街外两栋楼突然塌了,八个人没了命。普莱斯从里找了点灵感,写出了书里的人物菲利克斯·珀尔。为了写《拉撒路人》,普莱斯回到熟地方,也用了些新鲜事儿,参加了反暴力、管青少年成长的本地组织会,还坐着一位殡仪师的灵车看了会儿。这些经历给了书里的卡尔文·雷和戴维斯。至于书的主线和主角,则源于一条新闻:个孟加拉女工在工厂塌了后被困在废墟里,十七天才救出来。这给了普莱斯书里的“被救之人”安东尼·卡特。普莱斯在《拉撒路人》里写的,是那些日子不稳定、被边缘、大多过了年岁的人。他笔下的哈莱姆,也是座变来变去的城市。普莱斯看着无数因警察乱来**的暴力循环,大家更警觉、更生气了,他挺高兴。但他也不适应美国社会这套价值体系。亚当斯觉得普莱斯写书费这么久,是他们俩都在“使劲理解”美国在种族、阶级、警务这些话题上的话路。普莱斯最后把《拉撒路人》故事定在2008年,他还能“看懂”的年头,“话还没这么死板,没那么多不能写、不能碰的”。他想写的是自己刚认识哈莱姆那会儿,“我还有点自由”。普莱斯在这本书里暗含个意思:就算写的不是自个儿那路货色、生活,他还是有资格去记。书里角色菲利克斯·珀尔被问到为啥不征人就拍人,他回话:“我没法替别人说话……但我拍下他们,是为了提醒自己,我曾走过哪些路。”这话,差不多能当普莱斯本人的创作宣言。他的小说一直在谈城市生活的不平等,但他上街找故事的动机,是为了记——记他碰到的人的经历,也是他自个儿经历。《拉撒路人》最后**出来的,像接近摄影的结构——一幅幅人际关系和内在矛盾的速写,没啥要解的谜题,*没啥终点。小说里名义上的主角安东尼·卡特,在爆炸事后被请去社区会发言。他对吓傻的街坊们说:“我只记得,当我终于吸到口没混着土的空气时,我只想活、活、继续活。”但小说结尾,他从死亡边上逃回人世,好像也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还盼着“下一场偶然的对话能**点启示,能指引他活出个新鲜样”,可始终没成。临走前,我让普莱斯和亚当斯陪我去玫瑰园转转。那天特冷,花园挺冷清,离开花还早呢。亚当斯在冻土里往前走,一边指着园子角落,说等天暖了,她要把那儿好好拾掇拾掇。早些时候普莱斯跟我说他和亚当斯曾从东哈莱姆走到南布朗克斯的莫特黑文。他说那趟路印象特深——早些年他当少年时躲得远远的地界,如今被地产商又整出了诱人的名堂,**“钢琴区”,街边是新开的精品店。他叹气说:“房地产其实就是种暴力——它撵走人、毁了社区,或者说,硬把社区改头换面。”他说,他祖父母那辈儿、父母那布朗克斯,早没了,甚至更糟的是,“那地儿像被人往脸上糊了一层厚厚的舞台妆。”他还记着,有回在阿波罗剧院门口,碰巧听见个导游带着一群中西边游客讲:“我得提醒大家,好好瞅瞅你们眼前的这堆玩意儿,因为等你们下次再来——要是还有下次的话——这些都没了。”
广告
广告